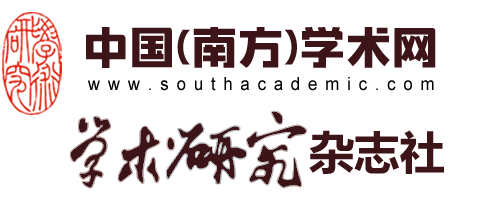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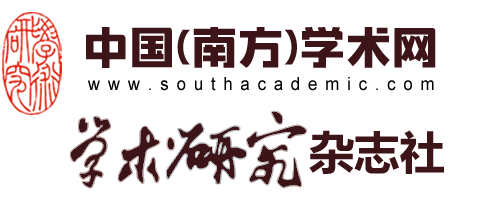
温朝霞,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探求》杂志教授。
[摘 要] 基于生产力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演化,文化生产形态也不断变迁。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演化至今的一种高级形态,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原始化文化生产和商品化文化生产。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的高级形态,既得益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升级形成文化新业态,又以文化的力量培育新质生产力。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来看,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产业之间存在天然耦合性。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赋能文化新业态,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反过来,文化产业本身所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创新精神,能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与活力,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 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文化生产形态 文化产业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特别是针对新一轮技术革新的浪潮而提出来的新概念、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论断,是对生产力发展变迁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力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必然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以技术与文化融合为特征的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是具备强大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的高级形态,既得益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升级形成文化新业态,又以文化的力量培育新质生产力。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也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是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有效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认同的一种能力。从文化产业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发展和演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推动文化生产形态跃迁的结果,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理。
一、文化生产形态的内涵与变迁
文化生产本质上或者狭义上就是指艺术生产。之所以使用文化生产这一概念,是因为文化产业的兴起、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艺术的内涵与外延发生扩散。因此,文化生产的概念比艺术生产更合时宜。文化生产形态是指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是文化生产方式的概括和总结。文化生产方式的变迁是文化生产演化的观照,基于生产力的变迁,不同时期文化生产的总体性特征不同,即文化生产形态不同。
马克思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视角,将艺术(精神)生产划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描述了艺术生产由非生产性阶段走向生产性阶段的演变过程。分析文化生产形态的变迁问题,这要基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的精神生产理论和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中的非生产性劳动生产艺术商品是为了交换获取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再生产的生产资料;生产性劳动生产艺术商品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3]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分析,聚焦于文化生产发展的三个时代:赞助时代、专业市场时代和专业公司时代。[4]生产性文化生产背后的资本逐利获取剩余价值的逻辑,使得文化生产主体艺术家成为资本雇佣的劳动者,文化生产从传统的个体化或手工作坊式的文化生产演变为工业化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文化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具体化,出现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专业公司。因此,生产性文化生产是文化生产形态演变为产业化文化生产的标志,也是界定文化产业的本质。从整体来看,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的现代表现形态,之前是商品化的文化生产,再往前追溯就是文化生产的起源即原始化的文化生产。
与物质生产方式一样,文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包括生产主体(艺术家等)和文化生产工具如媒介技术;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典型表现为文化生产的组织方式。文化生产形态大体上分为原始化文化生产、商品化文化生产和产业化文化生产。首先,原始化文化生产即艺术生产的起源。原始的艺术生产是依附于宗教祭祀、娱神等具有实用性,不具备独立性,且是混合性的形态。“艺术存在的最早的形式正是从非艺术向艺术过渡的形式,它具有双重的规定性和双重功能性。”[5]因此,艺术生产的起源是从娱神走向娱人,获得独立性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从混合性艺术解体为不同艺术样式的过程。其次,商品化文化生产。该阶段艺术的功能从娱神变为娱人,表现为简单的商品交换,艺术家出售文化产品换取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再生产的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剧院、歌舞场、妓院等等的老板,购买对演员、音乐家、妓女等等的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6]最后,产业化文化生产。作为文化生产体系中的“高级”形态,它超越前两个阶段,使得文化生产主体由艺术家变为资本,文化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组织形式及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更加细化,催生文化中间商即新型文化媒介人这一职业群体,且在文化生产中越来越占据枢纽地位。
二、文化生产形态演化的动力机制与文化产业化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文化生产形态的变革体现为文化生产主体的演变、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组织形式社会化等。这一系列表现背后的动力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文化需求不确定性和利润最大化催生的标准化文化生产方式;其二,工业化生产方式催生文化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其三,媒介技术作为文化生产工具,是实现文化生产方式革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具有逐利性的资本成为文化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媒介技术是实现产业化生产的催化剂。
首先,文化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催生文化生产的复制化和标准化。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提升,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革新;反过来文化生产方式的革新又形塑新的文化需求。文化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文化生产商(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文化生产过程中追求对“成功配方”的复制和模仿。作为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文化生产形态的独特之处为:它以最广大的普罗大众为消费对象,其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大众消费者的喜好,实现市场规模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标准化、复制化成为文化生产的基本模式。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其产品的模式化,另一种是生产方式的标准化,文化生产按其所需地对各种要素、原料进行分类、组装和拆卸。”[7]
其次,工业化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个体化生产,带来文化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劳动分工与庞大复杂的文化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相适应。随着工业化发展,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文化生产各个环节的关联度愈发紧密。因此,以往简单的个体化和手工作坊式的文化生产被集创作、制作、宣传、流通等环环相扣的严密的文化生产系统所取代。正是这种标准化和规则化的艺术生产方式,以及同一化的生产逻辑和加工原理,使文化的工业化成为可能。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企业,具有集体性和标准性,排斥个性和创造性,艺术家作为雇佣者是公司的集体成员之一,成为公司就业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艺术生产的原则来讲,艺术创作追求原创性和创新性;而文化产业的生产趋势是以复制和拼贴为主,对已有的风格和形式进行改造即“后制品艺术”。后制品艺术家创作的逻辑就是混合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叙事可能性,艺术作为一种用途被使用。后制品时代,艺术家复制、加工、重新编码、再现别人的作品,颠覆“独特”和“创作”的概念。艺术的问题不再是要做什么新东西,而是要用这东西来做什么。当今艺术家不再构造形态,而在编排形态。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将文化发展史概括为集体化—个性化—再集体化的演变过程。其中,古典时期的创作是集体主义的;在工业化萌芽阶段,面对新兴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冲击,浪漫主义者们高扬个性化创作的旗帜,以此作为对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方式的抵抗;然而,随着工业技术的日益精进与深度渗透,文化创造逐渐融入了文化生产的范畴,强调效率与规模。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文化形态崛起,其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回溯至集体生产的模式。“只是文化产业的新集体不同于古典时期的旧集体,因为文化产业的严格分工瓦解了传统艺术创作的统一性,同时产生标准化(当然标准化并不必然导致非个性化)。”[8]
最后,媒介技术作为文化生产工具,是实现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媒介技术是实现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手段,通过改变文化生产方式介入文化生产的历史。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媒介即讯息,表明媒介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9]客观地看,媒介技术是推动文化生产形态演化的直接动力。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工具,同时它还决定文化的类型。印刷术作为一种机械复制技术,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字书写的垄断,提高了普通民众的书写能力,进而扩大了文化消费群体,提高了民众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欣赏能力。所以,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讲,印刷术的出现对于文化消费者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使得少数精英的文化消费走向大众文化消费。电子媒介技术突破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限制。网络新媒体技术建立了新文化生产方式,模糊了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显著区分,使得生产和消费相混合,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化生产走向大众文化生产。但是,根据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划分的技术演进三阶段:玩具—镜子—艺术,这一过程当中艺术本身和非技术的社会因素也是必要的。无论技术有多么大的调适能力,它并不足以完成伟大的叙事,酿造醇香的美酒还是靠人的头脑。“有线电视得天独厚的优势使《黑道家族》这种形态的电视连续剧成为可能。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得天独厚的特征是产生《黑道家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余条件是剧作家、演员和制片人。”[10]尽管媒介产业如电影电视产业等都是技术催生的结果,但是就其根本来讲同样离不开艺术生产,否则就只是停留在媒介技术的初级阶段——玩具阶段,而无法演化为艺术。
三、文化产业作为高级文化生产形态的“新”与“质”
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力跃迁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也深刻影响着精神生产领域,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生产力推动文化生产形态跃迁的必然结果。作为高级生产力形态的新质生产力与作为高级文化生产形态表征的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文化产业作为高级文化生产形态,其“新”与“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力跃升的结果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文化产业的形成是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并促使文化生产形态跃迁的结果,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文化生产形态演化至今,其表征就是文化产业。20世纪文化大转型的标志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较之于传统手工作坊时期,文化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分散的,文化生产主体是艺术家,文化产品的存在方式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绘画、雕塑、戏剧、文学、建筑等艺术门类;而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复制性、市场化是其典型特征,文化生产的主体以创意阶层为主,文化产品的存在方式也发生剧烈的演变。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文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当中,从原始艺术的混合性到艺术的混合性解体,出现专业化分工,产生不同门类的艺术形态,再到不同艺术门类出现新的融合。相较于过去文化存在方式的演变过程,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让整个演变历程发生纷繁复杂的变化。这种文化存在方式的多样化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文化产业不断转型和升级,满足不同文化消费需求的根本。文化产业的母体是艺术,经济资本的逐利性和媒介技术的进化参与、革新艺术的生产形态催生了文化的产业化运作:以艺术为核心,以文化中间商为枢纽的严丝合缝式的系列化、复制性、标准化的文化生产体系。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对于艺术而言,其本质是中性的。因为即使最简单最纯粹的艺术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融入劳动分工与写作的元素,进而形成产业。所以,文化产业并非艺术的敌人,应该丢弃有史以来对文化产业的偏见。
(二)文化产业是文化物质化与物质文化化的新经济引擎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体系的一种“高级”形态,关于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一直众说纷纭。但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来审视,文化产业应该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逐利性;第二,复制性、标准化和系列化生产模式;第三,以文化中间商为核心的严丝合缝式文化生产系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尽管文化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呈现开放性,催生出文化新业态,但整体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化生产形态必须具备上述特点。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的历史脉络中的一种高级形态,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组织组成的复杂性生产体系。赫斯奇(Hirsch)将产业视为体系,即“产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组织,这些组织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投入),以某种方式经过转换(生产),然后将结果(产出)传送给下一个组织或市场”。[11]大卫·赫斯蒙德夫的《文化产业》衡量文化产业变迁所得出的结论是,充足的延续因素打破了我们已经进入文化生产新时代的假设。因此,20世纪中期就已建立起来的文化产业的根本特征仍然存在。如电脑游戏是一个有着新文本、新类型的新产业,但该产业在形成初期便建立在与许多其他产业同样的生产原则之上。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它将新的文化形式(如聊天室)带入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之中。它填补了其他文化产业的空白,而非取代或转换它们。当下文化产业的融合表现之一是文化形态的融合。
文化产业是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本身共同作用的产物,兼具政府文化意志的体现与资本增值的推动,因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双重属性。尤其是艺术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决定了文化产业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文化产业是标准化和个性化两股力量较量下的产物,标准化使得产业化成为可能,个性化使其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因此,标准化与个性化融合所产生的类型化是文化产业的典型特征,也正是艺术的个性化决定了文化实现产业化的同时,保持其独有的美感性。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批判性“文化工业”理论的逐渐式微,文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席卷全球,其影响力深远且广泛,使得文化的地位从马克思所阐述的“上层建筑”范畴,悄然渗透并融入了“物质基础”的广阔领域之中。这一转变,标志着文化不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与表达,而是与经济、政治、旅游等多个维度紧密相连,共同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架构。拉什(S. Lash)和卢瑞(C. Lury)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变迁的脉搏,提出了“全球文化工业”的新概念。[12]在他们看来,早期的文化工业虽然也涉及生产、流通与消费等多个环节,但其文化内核仍被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全球文化工业则截然不同,它通过将文化深度融入物质世界,实现了文化物质化与物质文化化的双重过程,使得文化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由此,文化产业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政治、旅游、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整体。“文化产业是一个社会系统。它的进化和一般物种的进化不同,不是整体性进化,而是渐进性的结构性进化。它是以一个业态、一个业态进化的。这种进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直接关联。”[13]但是,从文化生产形态来讲,文化产业作为一种高级形式,不管是传统文化业态还是文化新业态都是在一套复杂、严密的文化生产体系中运作。
(三)文化产业的特征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
文化产业无污染、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特点与新质生产力数字化、绿色化、高质量的趋势高度契合。因此,这种契合性分别体现为无污染与绿色化、高科技与数字化、高附加值与高质量之间的紧密贴合。
第一,无污染与绿色化的契合。文化产业的无污染性体现为:文化产业作为典型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它主要依赖创意、文化和知识产权等非物质资源,不直接产生大量的物质排放和环境污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与文化产业的无污染性不谋而合,共同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文化产业在核心价值、生产方式、产品形态、消费方式、产业链和商业模式等方面都显著不同于传统工业模式。这种差异使得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
第二,高科技与数字化的契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创作手段和表现形式,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之一,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和运营,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和决策效率。这种数字化趋势与文化产业的高科技性紧密相连,共同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14]他还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15]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边界日益模糊,“文化+”的跨界融合成为常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工具。这些技术不仅降低了文化产品的创作门槛,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极大地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背景下,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型文化业态应运而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中国文化产业新业态正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呈现多元化、融合化和数字化的发展特点。
第三,高附加值与高质量的契合。文化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以创意为核心,将原创性、文化带入生产和服务过程,使其发挥创造产值的功能。这种创造产值的活动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新质生产力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这种高效益的特点与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相契合,共同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数字艺术、数字博物馆、短视频到IP孵化,中国文化产业新业态涵盖多个领域。一方面,结合科技元素开发文创产品,如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文化衍生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另一个方面,从内容创作、生产制作到宣传推广、衍生产品开发等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的价值最大化。这足以证明,文化新业态在文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升级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契合关系。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精神力量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高附加值体现在文化产品与服务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创新创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市场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为承载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革新、要素耦合创新和产业迭代更新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高度契合性不仅体现了两者在发展理念上的相通之处,也为两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化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等手段,不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而新质生产力则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强调通过实现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创新性地配置生产要素,以及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升级,来显著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因此,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创新与升级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的互促发展
如前所述,从基于生产力推动文化生产形态变迁的文化产业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必然性、理论逻辑与现实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持续进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互促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17]如何把握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以推动两者的互促双强、协同发展成为关键。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助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种推动力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革新上,更深刻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引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从我国现行产业分类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科技服务业以及“三新”经济活动中的许多门类范畴都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数字创意产业、“三新”经济活动中的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数字动漫制作、数字游戏制作服务等。这些由重大技术突破或巨大社会需求带动产生的新兴产业,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内容表现,也是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的重要应用场景,从而成为塑造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支撑。
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产业具有天然耦合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与主攻方向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业态。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了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增强了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人工智能、AR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文化产业生产方式的创新。例如,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舞台演出领域,“数字演员”表演告别了真人表演形式。“数字梅兰芳”以数字化形式重现戏剧大师梅兰芳的声音、形体、神态、表演等,实现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创造性转化。新质生产力还打造了文化消费新模式。数字化的本质是去边界化。元宇宙、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数字技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实现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改变了景观设计和视觉呈现的方式,增强了游客的沉浸感和参与感。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传统文化资源得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如数字博物馆、在线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的实施,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到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网络游戏逐步从“娱乐化”向场景化转换,引发传统游戏圈的破壁,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场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在文化新业态的浪潮中,传统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消费者不再仅仅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摇身一变为主动参与者,享受着与创作者并肩共创价值的无限乐趣。沉浸式演艺更是将观众的角色升华。观众既是观赏者,又是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亲身参与,深度沉浸。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互动短视频、互动小说、互动网络剧等新型文化产品应运而生。受众在这些平台上不仅消费内容,更通过互动形成紧密的社群,共同推动着“共创式”文化消费新模式的兴起。
(二)文化产业创新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文化产业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18]而文化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新质生产力既是科技驱动的生产力,也是文化驱动的生产力,是科技与文化双轮驱动的生产力。”[19]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组合,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质量。文化通过其体现的智慧和价值观念,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推动科技、产业等领域不断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发挥文化的创新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升级。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在文化产业中,艺术、设计、传媒等领域的创新活动层出不穷,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文化产品的种类和形式,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模式变革。例如,数字技术的引入使得文化产业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实现全球化传播和个性化定制,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此外,文化产业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挖掘和整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将其与现代科技、创意设计相结合,打造出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还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业不断挖掘和培育新的文化元素和符号,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意源泉。文化产业创新正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核心驱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与品质的卓越提升。这一引擎的运作深深植根于技术的革命性飞跃之中,通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重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度革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能。在推动文化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互促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文化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更要聚焦于数据、大模型、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集成与应用,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这一融合应贯穿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与全过程,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注释
[1]《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第1版。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9页。
[4] [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第三版)》,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8页。
[5] [俄罗斯]卡冈:《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58页。
[7]单世联:《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8]单世联:《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第345页。
[9]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10] [美]保罗·莱文森:《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迁》,《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11] Paul M. Hirsch, “Processing Fads and Fashions: An Organization–Set Anan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7, no.4, pp.639-659.
[12] [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3]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 政策 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
[14]《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年9月19日第1版。
[15]《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3月22日第1版。
[16]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1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11页。
[18]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19]祁述裕:《培育新质生产力: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学术研究》,国内邮发代号:46-64,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学术研究杂志社门户网站:中国(南方)学术网http://www.southacademic.com,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手机版 | 归档 | 关于我们| (粤ICP备14048290号 )
主办: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B座7楼学术研究杂志社
邮编:510635
© 学术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