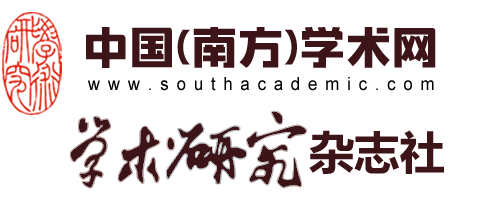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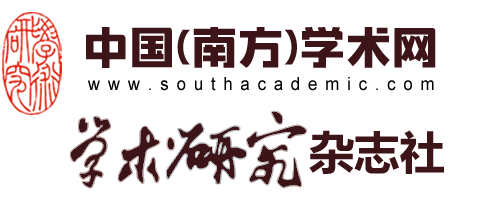
宋可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北洋”的本义往往为各种歧义所掩盖。揆诸史实,鸦片战争以前的“北洋”,受康熙开海、漕粮海运等王朝海洋政策的影响,多用来指称江苏以北(含江苏)的近海海域。鸦片战争后,随着海疆危机全面爆发,清政府被迫调整传统的海疆观与海防体制,“北洋”一词的涵义逐渐由海运贸易范畴转为海疆安全范畴。历经同治、光绪时期多次海防大筹议,“分洋分防”“北洋优先”最终确定为晚清海防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推动清廷海防战略的重心不断北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北洋”指称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海疆的用法趋于固化,其作为晚清海防体制改革代名词的地位亦由此奠定。“北洋”概念的嬗变,折射出清季海防体制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历程以及清人对海疆认知的持续深化。
[关键词] 北洋 晚清 海防 近代化 概念史
“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然而“北洋”的本义往往为各种歧义所掩盖。尽管有学者对晚清以来“北洋”一词的涵义及应用作了探讨,[1]但对于“北洋”概念生成、演变的历史线索仍缺乏细致的交代。另一方面,由于学术视角的差异,传统学界多从职官、外交、洋务、政府的角度来考察近代“北洋”语义的变化,而普遍忽视了这一概念的基本义项——作为海洋或海疆范畴的“北洋”,更未注意“北洋”概念流变与晚清海防体制转型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察。从这一意义而言,追溯“北洋”概念的历史本相及其演变逻辑,理应成为“北洋”研究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藉此不仅有助于廓清“北洋”概念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晚清海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
一、鸦片战争前“北洋”概念的历史结构
根据张华腾的研究,“北洋”一词最早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2]郭卫东、王先明等提出,历史上的“北洋”,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3]笔者认为,以上对“北洋”概念源头、涵义的解释皆不准确。揆诸史料,“北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御史中丞沈与求奏言:“臣闻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陈贴、通明镇等处,次及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4]从字面意思分析,时人将今天长江口到钱塘江口之间的苏州洋海域分为南、北二洋,其“北洋”意指长江口附近海域。这一结论在同时期其他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明州人王伯庠记该州形势称:“郡当海道之冲,界乎北洋。”[5]宝庆《四明志》将长江口附近的三姑山(即今大洋山)记为“北洋冲要之地”,朝廷在此山设寨驻军,以“防守北洋要冲”。[6]上述史料,皆将明州以北的长江口海域定义为“北洋”。盖南宋政权偏安东南,海防成为国防的重要方向,而两浙地区的海疆安全,尤关乎王朝政权安危,以故出现了以两浙为中心视角区分海洋畛域的现象。
宋元之际,“北洋”的地域指向逐渐向北转移。文天祥《北海口》诗序云:“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人趋江南,而经北洋者,以杨子江中渚沙为北所用,故经道于此,复转而南,盖辽绕数千里云。”[7]很明显,文天祥将黄、淮之间的海域划分为南洋和北洋,航海者经此“北洋”,方入山东地界。刘迎胜认为该处所指南、北洋“与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南、北洋相当接近”,[8]实际上并未注意到文天祥的论述是针对“淮海”而言的,故误将此“北洋”与清末的“北洋”相对应。
元明时期,随着海运的勃兴,典籍中关于“北洋”的记载不断增多。元人朱德润云:“至正八年春,海寇窃发,公亲率所部,出刘家港迎贼捕敌,(贼)潜入北洋诸岛。”[9]明人陈全之在《海运胶莱新河》中写道:“海运惮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门,此两险多碛。又成山突出,当东洋之冲。沙门旋扼,处北洋之腹。”[10]其所谓“北洋”,指的是山东附近的黄、渤海域。嘉靖中期以后,倭患频仍,明廷对海洋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由此出现了依据海洋地理环境特性和航行条件划分南、北两洋的说法,如郑若曾称:“沙船能调戗,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盖北洋浅,南洋深也。”[11]郑氏所言“北洋”虽无确切的地域指向,但推测来看,当与黄、渤海域相去不远。除此以外,在地处抗倭前线的浙、闽等省所辖海域内部,亦出现了南、北洋之分。如万历年间,明廷在浙江沿海设二游击,“嘉、宁(二府)以北,是为北洋,北游领之;台、温(二府)以南,是为南洋,南游领之”。[12]
入清以后,“北洋”一词在时人认知中进一步清晰起来。总体来看,“北洋”在当时有两种并行不悖的解释。一是以“北洋”指代北方近海海域。以“北洋”泛指北方近海海域认知的兴起,与清前期的开海举措密切相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台湾平定,海疆宁谧,诏开海禁,凡“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13]尽行停止。随着海禁政策的结束,南北向的海洋贸易迅速发展,清人形容“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14]成书于康熙末年的《台海使槎录》记载这一现象称:“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至)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鞋、布匹、碗纸、糖麯、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15]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藉南北海运贸易为生的群体,所谓“沿海编氓,自开北洋海禁以后,造船出海,各随地产土著,贩运懋迁,迄今二百年来,藉此谋生”,[16]而以“北洋”指代北方近海海域的观念,也逐渐在民间形成。其中,著名经世学家包世臣对“北洋”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在此包世臣对“北洋”给出了一个清晰定义:以上海吴淞口为界,凡吴淞口以北的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四省海域为“北洋”,以南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海域为“南洋”。包世臣对南、北洋划分理念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深刻的经济地理现象。清中期以来,原南北海运的重要中转港口浏河港因泥沙淤积,日益衰落,南北商船多云集上海,从事转口贸易,据记载,“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17]至嘉庆、道光时期,上海已发展成为南北海运贸易的中转枢纽,这就刺激了以上海为中心视角区分南、北洋观念的形成,人称:“(上海)居南、北洋之中,其形势非屹然重镇哉。”[18]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北洋”观念皆属民间层面。而官方对“北洋”概念的接受和使用,则受到了嘉庆、道光时漕粮海运的直接影响。嘉庆十六年(1811),两江总督勒保等上疏反对漕粮海运,其中提到,“闽省惟赴津大船,始谙北洋水道,而此等大船为数无多,亦属不敷供运。至粤省相距更远,其船向不能北行。是闽、粤大船,亦未可雇用”。[19]这是作为海运贸易概念的“北洋”一词首次出现在《清实录》这一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官书中,预示着“北洋”概念逐渐由民间转入官方视野。
至道光时期,“北洋”在官方文书中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反映了漕粮海运议题在国家政务中的重要性。林则徐《筹画漕务疏》说:“南、北洋面,沙船、鸟船,各有所宜,本难越驶。”[20]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亦称:“闽、粤南洋,或有海氛,而由吴淞口迤北,北洋沙礁水浅,南洋鸟船断不能入,从无他虑。”[21]从中可见,高级官员对“南洋”“北洋”的说法已相当熟悉。更具典型意义的是道光帝在道光五年(1805)颁布的要求沿海各省试行海运的谕令,内云:“朕思江苏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22]这表明“北洋”概念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与当时流行把江苏海域纳入“北洋”范畴的认知不同,道光帝将“北洋”仅仅定义为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海域,表明统治阶层对“北洋”的确切所指,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二是以“北洋”指代闽、浙两省的北部海域。除了以“北洋”指称北方近海海域外,鸦片战争以前,沿海七省中的闽、浙两省亦有着明确的“北洋”指属。以福建省而言,康熙五十六年(1717)奏准:“海坛、金门二镇,各分疆界,为南北总巡,每岁提标拨船十只,将六只归于巡哨南洋总兵官调度,四只归于巡哨北洋总兵官调度。”[23]以此为标志,福建海域遂横向分为南、北两洋。福建水师提督每年先前往“南洋”,巡视“金门、铜山、南澳等处”海域,之后前往“北洋”,巡视“海坛、闽安、三沙、烽火门等处”海域。[24]浙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于时浙江海域由定海、黄岩、温州三镇负责管理,而三镇所辖海域,各有“南洋”“北洋”之分。如定海一镇,“南洋三百余里,至定镇中营汛内之牛栏基,而与黄岩镇接界;北洋四百余里,至定镇左营营汛内之大衢山、右营汛内之大羊山,而与崇明镇接界”。[25]乾隆十五年(1750),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疏请改革巡洋会哨制度,令“浙省定海镇,先巡北洋,与江南崇明镇会哨于大羊山;后赴南洋,与黄岩镇会哨于石浦港;黄岩镇则先巡南洋,与温州镇会哨于沙角山。后赴北洋,(与)定海镇会哨于石浦港;温州镇则先巡北洋,与黄岩镇会哨于沙角山;后赴南洋,与闽省海坛镇会哨于南关”,[26]浙江海域的“南洋”“北洋”划分至此进一步制度化。郭卫东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温州镇总兵刘文敏奏称前往“南洋”“北洋”会哨一事为例,[27]认为清前期“北洋”的地域指称仍含混,时在“浙江等南方地界”,[28]这一误判实际上是未对闽、浙两省的海域管理制度进行细致考察所致。
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以前“北洋”概念的形成与流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洋”的地域指向整体上呈现出愈加清晰的态势。那么,进入近代,在清王朝的海疆安全遭遇严峻挑战之际,“北洋”概念在时人认知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历史机制?
二、海疆危机背景下“北洋”概念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来自海上的威胁不仅使清朝的东南壁垒倾塌,其北方海疆也处于“岛夷”的窥伺之下,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一时期关于海疆安全状况的官方文书中,经常提及“北洋”一词,从中不难看出清政府对北方海疆的重视程度。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主持浙江军务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向朝廷奏陈沿海各省地势情形,特别提到了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四省的海防特点,如江苏“除吴淞口、崇明、宝山最为险要外,其淮、扬、海三府州所属洋面,外无屏蔽,潮来甚溜”,山东“登、莱二府之成山,虽陡入东海,而非通商马头,不过为南北往来之标准”,直隶洋面“外有旅顺口、登州府城,南北对峙,中间山岛林立,洵为天险”,奉天“所属各港,口门均浅,且有线沙,为闽、广南洋鸟船所最畏”。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北方近海海域的特殊属性,“是以海贼蔡牵等,滋扰浙、闽、粤三省十余载,从无扰及山东、直隶、奉天之事。即北洋贸易,亦均系平底沙船,其闽、广南洋鸟船赴关东者甚少。盖北洋之情形,与南洋之情形迥乎不同,南洋多石岛之明险,而北洋多沙线之暗险,夷船畏暗险甚于明险,并非处处堪虞,港港可入”。[29]裕谦明显借用了清中期以来流行的“北洋”说法,即以“北洋”指代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四省海域。
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北方沿海各省督抚的疏文中,亦多次提到“北洋”。道光二十一年,奉天将军耆英疏称:“盛京为根本重地,尤当严密防守……现据镇海县报有夷船四只,宁海县报有夷船一只。其余由厦门驶向东北外洋船只,是否窜入浙境,抑或潜赴北洋?亟应慎密防堵。”[30]道光二十二年(1842),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言:“南北省海岸口门深浅不同……北洋情形,度其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31]同年,山东巡抚托浑布在奏折中说,如在东省长山岛“扼要之南城分设一汛,外足以控制北洋,内足以捍卫郡垣,声势较为联络,巡防可期得力”。[32]尽管三省疆臣未对“北洋”进行清晰的定义,但此三省海域属于“北洋”范畴是显而易见的。
整体而言,随着鸦片战争时期海疆危机全面爆发,“北洋”进一步进入国家官方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北洋”概念的两个转变趋势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第一,由海运贸易层面的“北洋”转变为海疆安全层面的“北洋”。前节已述,鸦片战争以前时人认知中的“北洋”,基本是和海上贸易、漕粮海运联系在一起的。至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首次突破山东海域,逼临直隶,威胁京师以及盛京,引起朝廷震动。在战争中,清政府注意到黄、渤海域的海防建设长期滞后,如何应对西方人从防御薄弱的黄、渤海域入侵京畿,成为朝堂的重大议题。如奕经上呈了奉天、山东两省的海防方案:“奉天地面,西南环海,旅顺水师营独当其冲。面前南、北隍城二岛,距该处水面一百八十里,奉天、山东两省分辖会哨。此二岛北与旅顺、铁山对峙,南与登州、庙岛对峙,凡商船往来天津等处,必由诸岛左右经过,实为南来海路要隘……该处若预为把守,安设炮位,添驾船只,两省声势联络,巡逻哨探,迎击邀归,该夷断难阑入。”[33]道光帝亦提出自己的看法:“盛京旅顺口与山东庙岛相对,其间海面相距百数十里,为海舶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设兵防堵,其势有所难及。朕闻夷船坚固,惟于夜间从后尾轰击,较可得力……遇有夷船停泊该处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绕至船尾,开炮轰击。”[34]
在朝廷密切关注北方海疆安全的背景下,“北洋”概念的指向逐渐由传统上的海域嬗变为具有浓厚海防意蕴的海疆。[35]如奉天将军耆英称:“奉天海疆,原系北洋,一经北风司令,各口船只渐次南旋。且每届冬令,除金州属之和尚岛二三处尚有驶到商船,其余各口,并无船只停泊,是地势天时,原与南洋不同。奴才自上年督办防堵以来,悉心体察情形,分兵置炮,似可无虞疏失。”[36]耆英语中的“北洋”显然不仅仅是以往认知中的北方近海海域,而是包括了海域、海岛及沿海海防要地在内的整个北方海疆。
第二,“北洋”涉及的地域,逐渐从广义上的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四省演化为环渤海的山东、直隶、奉天三省。这一变化,实际上与第一个转变趋势直接相关。战争时期英军舰队对京畿附近海域的袭扰,促使清政府开始着意加强环渤海地区海防机制的内在联系。从海疆形势来看,环渤海的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共为唇齿,“相连而不可离”,[37]时人形容,“登州突出海岸,距旅顺二百五十里,中间岛屿错落,横如阃限,是造物者特设此险,以卫北洋门户”。[38]从战争结束后环渤海三省督抚的海防筹议奏疏中,不难看出其已经意识到三省海上防务的一体性。如讷尔经额指出:“天津密迩京师,其海防倍重于东南,而与东南各省情形亦迥不相同。盖山东之庙岛,奉天之旅顺口,遥遥相对,宛若门户。窃见北洋形势,不宜水战,而近畿重地,更不可轻于一试,总以贼不敢来,来不能入为上策。”[39]托浑布提到,山东形势,“据天津上游,为奉天咽喉”,若山东、直隶、奉天三省,“各于接壤洋面,增设水师,互相应援,则军威雄壮,籓篱自固”。[40]道光帝也意识到改革环渤海三省海防体制的必要性,道光二十二年谕令山东、直隶、奉天三省实行水师会巡制度,务使“三省洋面连为一气”。[41]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北洋”的地域指向,隐隐有将江苏排除在外的趋势。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已调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在变通江省水师营章程折中特别提到了“南洋”“北洋”的地域分野:“臣等以洋面有南北之分,以大江为界,江以南为南洋,水深而多暗礁,利用广东之米艇,福建之同安梭;江以北为北洋,水浅而多暗沙,利用江南之沙船。”同月又奏:“海洋亦以大江为限,江以南至广东皆为南洋,多暗礁。江以北至盛京皆为北洋,多暗沙。”[42]耆英以长江为南、北洋分界的认知,明显是历史惯性下作出的判断。随着清朝海防战略的要点由捍御东南海疆转向保卫京师和辽东等“根本之地”,“北洋”防务在国家海疆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长远来看,“北洋”概念涉及的空间地域,势必将剥离远离京畿、战略地位持续弱化的江苏。
值得注意的是,直隶、奉天两省因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故官方有时也会用“北洋”一词专指直隶、奉天两省海疆。道光二十八年(1848),因江苏、山东洋面不靖,盗案频发,道光帝下达指示:“该匪出自闽浙,流毒江苏、山东,设或此拿彼窜,阑入北洋,延袤四千余里,为害实非浅鲜。”[43]此处“北洋”,显然指山东以北的直、奉海疆。道光三十年(1850),上谕军机大臣:“有人奏,(奉天)盖平县、复州、金州厅、岫岩厅地方,时有海盗出没……该处额设水师兵船,自应实力出洋巡哨。海盗因山东捕拿严紧,窜入北洋,即宜扼要堵截。乃任其抢货杀人,毫无顾忌,实属废弛。”[44]其所谓“北洋”,亦不包括山东海疆。以上现象,凸显出这一时期“北洋”的概念使用广狭皆有,尚未形成统一规范。
到咸丰时期,“北洋”的用法仍集中在海疆安全层面。此时对“北洋”一词影响较大的,当属中英两国在清剿黄海海盗事件上的博弈。咸丰五年(1855),因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海运再兴。海盗遂在漕船必经的山东海域肆行掳劫,致使南北商船望而却步。英方借机向清政府提出可以派遣海军帮助中国剿灭海盗,朝廷和沿海地方对外国兵船企图阑入黄、渤海域的动机表示怀疑。两江总督怡良奏言:“英夷欲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署苏松太道谕令该夷毋庸前往”,咸丰帝对怡良的慎重举措表示赞赏,批示说:“英夷通商船只,止准在五口往来,山东、奉天洋面,皆非该夷应到之地。着即饬令将北驶船只迅速追回,不准擅向北洋开驶。”[45]
在清政府谨慎处置此事的同时,漕运总督邵灿向朝廷提出建议,谓欲清除盗踪,畅通海路,关键不在于借助英国兵船,而在于扼守“北洋”岛屿。邵灿指出,历年南北商船被劫失事之案,以奉天牛庄、山东石岛二处为最,破局之道,全在该管省份调拨水师战船,扼守牛庄、石岛等商船寄碇收泊之所, 奏请朝廷“敕下奉天、山东等省,筹议速办,以清洋面而利漕行”。[46]咸丰帝览奏后,向奉天、山东等省发出谕令:“邵灿奏由商捐雇网梢船二十只,与浙江商艇合力守驻(江苏)佘山,是南洋盗艇当可绝其来源。其北洋牛庄、石岛等处,亦应预筹扼堵。着英隆、书元、崇恩严饬水师将弁,实力巡哨,认真剿捕。务使匪船无从窥伺,以利漕行。”[47]
由这些公文可以看到,对于英国试图利用中英联合军事活动,扩大在中国海疆尤其是北方海疆的侵略权益,从朝中决策者到沿海地方督抚,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不仅会损害中国对海洋领土的管辖权,更会对“屏蔽畿辅”的“北洋”带来安全风险,[48]进而在现实层面对王朝的政权稳定构成威胁。不言而喻,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官方文书对“北洋”一词的频繁使用,指代北方海疆的“北洋”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为下一阶段“北洋”词义的演化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三、“北洋”概念的流行与晚清海防体制转型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经由“北洋”,进犯京师,咸丰帝仓皇北狩。清政府在黄、渤海一带的海防形同虚设,促使身处海疆危局中的精英阶层进一步思考中国海防体制的转型方向。在晚清最后数十年里,种种海防改革主张矍然而起,推动“北洋”话语进一步在朝廷内外流行开来,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政府海防体制改革的重要指标。
1860年,战争甫一结束,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上善后章程六条,其中包括在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以便于管理。就北方而言,在“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办理通商大臣一员,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其奏进,上谕内阁,正式任命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49]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官方已逐渐习于将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疆等同于“北洋”,故此三省沿海的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自然而然地被时人称之为“北洋三口”,如咸丰十一年(1861)崇厚奏云:“北洋三口,自本年开办以来,天津一口办有规模。”同一时期薛焕疏称:“北洋三口现有大臣,南省亦应一律设立。”[50]“北洋三口”之说的兴起,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以“北洋”指称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疆的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研究一般认为从1860年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到1870年改为北洋大臣,[51]是“北洋”由地域概念转为官职概念的重要节点。[52]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我们摆脱“预设前提”的分析框架,仔细检讨这一时期的史事本相,可以发现,突出的海疆属性才是晚清“北洋”一词最重要的内在特征。这中间对“北洋”概念使用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朝野对中国海防体制改革的讨论,尤其是丁日昌所倡导的“三洋分防”说。
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对中国近代海防体制的设计、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治六年(1867),朝廷预筹与西方各国修约事宜,令李鸿章等议奏,李鸿章以其密友江苏藩司丁日昌的条陈附上。在条陈中,丁日昌对明代以来中国传统海防体制的弊病作了全面检讨,认为以沿海炮台、近岸水师为经纬的分散布防体系不足以抗御外辱。为今之计惟有变革海疆军制,分建北、中、南三洋海军,以改善并强化海防,夺回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失去的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疏中丁氏对“三洋”的划分十分明确:直隶、奉天、山东海疆为“北洋”;江苏、浙江海疆为“中洋”;福建、广东海疆为“南洋”。[53]
丁日昌的海防筹议切中时弊,在热心洋务的官僚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两江总督曾国藩对丁日昌的观点给予了肯定,其在《复丁雨生中丞》中称:“外海水师,阁下统筹全局,拟建三阃,浙江、江苏建于吴淞,山东、直隶建于天津,广东、福建建于南澳,各备轮船十号,艇船二十号,专泊洋面,无事则承运漕粮,有事则首尾相应,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54]在之后曾氏所上的《覆奏筹备海防折》中,亦深刻体现了丁日昌“三洋分防”说的构想:“沿海之直隶、奉天、山东三省,江苏、浙江两省,广东、福建两省,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各应归并设防。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沿江三省,共练陆兵三万,统计每年需饷八百万两。”即将“北洋”三省的海防视作一个整体。不过,因此时清廷财力紧张,“无款可筹”,[55]丁日昌、曾国藩的建议只能暂时搁浅。
至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爆发,清王朝的海疆安全再次受到威胁,朝野大为震动,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在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不久,奕等奏《海防亟宜切筹折》,建议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详加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奏覆”。[56]丁忧在家的丁日昌获知此事后,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奏《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再次提出将全国海疆划为三洋布防的主张。具体方案包括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各一员,“北洋”提督,统山东、直隶海疆,[57]“建阃于天津”;“东洋”提督,统江苏、浙江海疆,“建阃于吴淞”;“南洋”提督,统福建、广东海疆,“建阃于南澳”。如此措置,可使“三洋联为一气”,[58]以严海防。
在清政府亟需对海防布局进行调整的背景下,丁日昌的“三洋分防”说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奕欣奏请饬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围绕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展开讨论。[59]沿海疆臣对丁日昌的观点多持肯定意见。浙江巡抚杨昌濬在奏覆中指出,“窃谓南、北、中三洋,宜设水陆三大枝,闽、广合为一枝,江、浙合为一枝,直隶、奉天、山东合为一枝。每枝精练万人为度,各设统领一员,帮办二员,仍听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外洋有此三大枝水军,练习三数年后,海上屹然重镇,可分可合,可战可守。近则拱卫神京,远则扬威海面,不惟内地之奸匪敛迹,外夷之要挟亦可渐少矣”。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称,“奉天至广东洋面,袤长七千余里,亟应联为一气,声息相通”,基于这一现实应“分海洋为三路,以奉天、直隶、山东为北洋,而分阃于大沽;以江苏、浙江为中洋,而分阃于吴淞;以福建、广东为南洋,而分阃于台湾,各设总统一员,作为海防大臣,沿海水师官兵,就近统归节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李宗羲原则上同意丁日昌的观点,不过他认为三洋分区设防,“造端闳大”,应请饬下廷臣,再行核覆。除此以外,闽浙总督李鹤年的建议也颇具价值,他将丁日昌的“三洋分防”改为两洋布局,即将全国海疆划为南、北两洋,其海防事宜分别由南洋、北洋大臣督办,“以重事权”。所建两洋海军由该大臣节制,每年分春秋二季会哨,“春至北洋,秋至南洋”。沿海各道兼理海防事宜,“无论本省邻省,均分隶南北洋大臣统属”,如此则“事权归一,各省联为一气,声息可以相通”。[60]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上的《详议海防折》。李鸿章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海疆形势来看,中国海岸线自奉天延至广东,“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必须重点分防。从这一意义出发,李鸿章虽然同意丁日昌的“三洋分防”方针,但对全国海防的重点自有一番主张:“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61]换言之,李鸿章认为与其他两洋相比,“北洋”三省的战略重要性无疑居于优先地位。按照他的计划,应“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62]基于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领袖身份,他的建议显然对清政府海防体制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综合各地方大员意见的基础上,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明发上谕,颁布了海防体制改革的方案:“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63]这是一道具有标志性的谕旨。它实际上调和了丁日昌“三洋分防”与李鸿章“北洋优先”两种主张,意在打破沿海七省之间的海疆畛域,把南、北洋海防分段督办,共同筹措海防定为国策。同时也代表以“北洋”指代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海疆,以“南洋”指代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海疆的认知通过官方诏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使其具备了规范层面的意义。李鸿章在此后不久所上的《督办北洋海防谢恩折》中称:“臣伏思今日中外交涉局势,为千古所创见,此间海防筹办机宜较他处而尤难。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别无可筹之款。”[64]这反映出“北洋”概念至此已趋于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清政府确定了两洋海防平行发展的方针,但从国家海疆战略全局来看,作为“畿辅重地”的“北洋”,其定位要高于作为“财赋奥区”的“南洋”。[65]时人云:“以形势言,则北洋较南洋为尤急。京师居中国,东北、天津居其前,为门户;烟台居其旁,为藩篱;旅顺居其背,为腰脊。而北洋独扼其冲,朝鲜又为北洋之门外。经营北洋,盖即联朝鲜之势也。联朝鲜,即以固东北之圉也。以北洋控朝鲜,即以朝鲜控东北。故曰防海,则北洋较南洋为尤急……俟北洋之防既固,然后徐图南洋,以成犄角之势,此亦先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66]关于这一点,负责“南洋”四省海防的沈葆桢在光绪元年六月亦坦陈:“外海水师,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力薄,而成功缓。”[67]盖两利相形,则取其重,“自应先北洋而后南洋”。[68]
由于“北洋”在决策视野中占有更特殊性的位置,因此经营“北洋”海防实际上成为晚清海防体制改革的重心所在。在这一时势的带动下,“北洋”跃为晚清沿海督抚讨论海防建设的高频词。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自不必论,其在公文往来中处处以“北洋”为重,如《请拨海防经费折》云:“北洋防务,屏蔽京师,关系全局。”[69]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指出,现“为北洋计”,“直、东、奉三省合力并谋,有铁甲船五号,中轮船十号,小轮船六号,分布于东之烟台、威海,奉之黑山湾,为北洋作一关键”,则进可击,退可守,“惟山东在北洋之内,所有一应经费应须取给北洋”。[70]两江总督曾国荃称,全国海防,“区分南、北洋”,而山东“归北洋兼辖”,闽、浙、粤三省“归南洋兼辖”。[71]统治者对“北洋”的海防事务也投以更多的关注,光绪帝曾多次下诏,声言“防务以北洋为最要”,“北洋为京畿门户,防务尤关紧要,筹备必须完密”。[72]之后,在中法战争引发的第二次海防大筹议中,清政府基于黄、渤海方向受到海防压力不断增大的现实,最终确立了优先建设“北洋”三省海防的方针。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五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重要的懿旨:“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73]从同治六年丁日昌首次提出“三洋分防”说,到光绪元年颁行南、北两洋海防平行发展的战略,再到光绪十一年确立优先建设“北洋”海防的方针,清政府依据海疆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其海防体制和重点布防区域,从中折射出清王朝积极构建海疆安全体系的努力,“北洋”作为晚清海防体制改革代名词的地位亦由此奠定。
自此以后,清政府加快了“北洋”海防建设的步伐。在陆上防务方面,因“北洋沿海地段绵长,要隘极多”,自山东沿海至奉天,“延袤几三千里,断难处处周密”,[74]故采取择要扼守之法。以淮军各营,“分驻直隶天津、大沽、北塘、芦台至山海关沿海一带,并奉天之旅顺、大连湾各海口,修筑新式炮台”,俾“北洋海疆千余里,有事得资援应”。[75]海上防务方面,积极推动北洋海军成军。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提交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建成。章程规定,北洋海军每年在春、夏、秋三季“赴奉天、直隶、山东、朝鲜各洋面以次巡历”,冬春之交,则“开赴南洋,会同南洋各师船巡阅江、浙、闽、广沿海各要隘”。[76]很明显,北洋海军的法定管辖、巡逻空间主要是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疆。关于此时“北洋”的范围,追随李鸿章经营“北洋”防务有年的薛福成在甲午前夕讲得十分清楚:“北洋海防,如金州、大连湾、大沽、北塘、山海关皆翼蔽畿辅,而要害则尤在左延之旅顺口,与右袤之登州成山卫、烟台、威海卫。”[77]语中所涉“北洋”地域,在在皆与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疆相关。
甲午一役,北洋海军付之一炬,然而时人对作为海疆概念“北洋”一词的使用并未戛然而止。相反,在清末舆论界掀起对“北洋”海战失利进行反思热潮的带动下,“北洋”进一步由庙堂走向民间,发为幕府中的策论、报章上的时文。著名维新家郑观应在其著作中重拾丁日昌的“三洋分防”说,将海疆“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78]不过,鉴于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因畛域太分而最终战败,郑观应提出之后若重建三洋海军,应效法西方,统一海防指挥体制,将其“归一水师提督中资格最深者统领,免致临时各督抚各分畛域,各船借词规避,再蹈前辙,互不相救”。[79]改良派思想家陈虬认为应分海疆为“北洋”“东洋”“南洋”“外洋”四洋,在四洋海军之上,“特简经略大臣以辖之”。[80]
亦有人对清政府此前“先北后南”的海防战略取向进行思考。如翰林院侍读荣光提出,以海防形胜而论,“莫过北洋”,但今昔形势不同,自胶州租于德,威海让于英,旅、大陷于俄而复夺于日,“北洋之险要尽失”,为此,中央政府应着眼于经营广东虎门、浙江沙门湾等“南洋之重镇”,以“控制北洋”。[81]
从现实来看,朝野关于“南、北洋海防,联为一气”的普遍共识最终影响了清末政府的海防政策。[82]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电谕裕禄、刘坤一,谓“北洋”“南洋”海防紧要,令二人“饬各该统将,常川于海口来往梭巡,南、北两洋互相会哨,以备战守”。[83]其语中颇有统筹两洋海防之意,惜因戊戌政变而止。至光绪三十年(1904),两江总督周馥奏称“中国从前创办海军,因限于财力,先办北洋,而南洋则因陋就简,规模未备”,现今时势各异,应将两洋兵船归并,由现充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统管,“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训练学生水勇,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可互相调用。见在兵舰虽不足一军之数,而统御巡防江海一军,有此以镇之,则均属堪用”。[84]上谕依准,于同年十二月授派叶祖珪“统率南、北洋海军”。[85]至此,中国的海上力量乃至海防体制终于在清末海防力量孱弱的背景下,实现了形式层面的统一。关于这一海防战略的重大调整,时论颇称之,盛宣怀云“南、北洋海军,现奏联为一家”,“合为一气”。[86]这不仅体现了此时清政府在海疆经略上的全局性规划,同时也折射出作为海疆范畴的“北洋”概念,并未随着晚清筹海图强运动的失败而消散。
四、结语
围绕本文对清代“北洋”概念建构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重要概念演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关键的历史转折。纵观“北洋”概念的历次嬗变,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以前,在康熙开海、漕粮海运等王朝海洋政策的影响下,“北洋”词义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江苏以北(含江苏)的近海海域。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中西海上冲突加剧,清廷面临严重的海疆危机,“北洋”一词的涵义遂由海运贸易范畴转为海疆安全范畴。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历经多次海防大筹议,“分洋分防”“北洋优先”成为晚清海防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北洋”指称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海疆的用法进一步固化定型。直至清末,“北洋”概念的内涵仍保持了以上基本面向。其承载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北洋”一词的嬗变,反映出清季海防体制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历程。对于清王朝而言,受明代倭患及明清之际早期西方殖民者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影响,其海防的重点方向长期在东南海疆。如康熙、雍正时人陈良弼称,在沿海七省中,海防之要“在乎广、闽、浙三省”,[87]江苏、山东、直隶次之,奉天又次之。清廷在绵延万里的沿海区域通过分散的军事部署,维持对海疆的弹压与控制,清人总结指出“置水师以镇之,炮台以守之,兵弁有制,训练有方,游巡有时,会哨有地,桨船、战船,星罗棋布,都守之上,辖以参游副将,统以提镇,又有兵备各道以分莅之,又有督抚以节制之”,使其“递相管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88]可以说,“南重北轻”“分散布防”是清前期海防体制两个最主要的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对传统的海防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为防止西人从海上进犯京师,拱卫京畿逐渐成为晚清政府制定海防政策的主要内容,导致其海防战略重心不断北移。其次,前近代时期“划界立汛,散而无统”的海疆军制,使清政府缺乏可以随时调动以应对海疆危机的海上机动力量,难以抵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以上现实,在客观上要求清廷必须改革以往的海防体制,克服“处处布防”“势分力弱”的被动挨打局面。[89]正如丁日昌在《海防条议》中指出的:“当令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畛域,何则?风涛驰骤,一息千里。若分各省疆界,则彼此推诿,寇盗终无殄灭之日。故化散为整之法,不特陆师宜然,而水师尤为切要。”[90]要言之, 只有建立全新的近代化海防体制——统一的海防决策和管理机制,才能打破七省海疆畛域,集中海防力量,从而在组织机制上保证清朝能够与列强在海疆展开博弈,夺回西方侵略下丧失的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所谓“万一强敌凭陵,则合南、北洋之力,可以一战”。[91]晚清“北洋”概念的嬗变与流行,正迎合了以上两大历史需求。
综上所述,从“北洋”词义的变化可以反映清人对海疆的认知不断深化。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在海疆地区整体维持了“海不扬波”的治世局面,时人多将“北洋”一词与海运、贸易等社会经济议题联系在一起。迈入近代,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未有水陆交逼、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92]清政府被迫调整原有的海疆观与海防体制。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传统将海疆分属七省的经略模式逐渐被“北洋”“南洋”取而代之。以两洋而论,则“北洋”又远居“南洋”之上。换言之,“北洋”已经从一个较为纯粹的地域海洋概念,演化为具有深厚政治、军事意涵的海疆概念,并且与国家安全、历史转折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此时在清人的认知中,海疆作为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真正纳入数千年未有的变局中。
注释
[1]陈佳荣:《宋元明清之东西南北洋》,《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9页。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王先明、杜慧:《“北洋”正义》,《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2期。郭卫东:《释“北洋”》,《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
[2]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3]郭卫东:《释“北洋”》,《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王先明、杜慧:《“北洋”正义》,《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2期。
[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58页。
[5] [宋]王伯庠:《西湖重修湖桥记》,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10《记》,《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62页。
[6] [宋]胡榘等纂修:宝庆《四明志》卷20《官僚》,《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247页。
[7] [元]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卷8《北海口》,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80页。
[8]刘迎胜:《中国古代图籍中的亚洲海域》,《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9] [元]朱德润:《资善大夫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买公惠政之碑并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28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14页。
[10]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3,《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11]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沙船图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80页。
[12] [明]沈守正:《雪堂集》卷6《新设台温南洋游击府公署碑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63页。
[13]《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巳,《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4页。
[14]谢占壬:《海运提要序》,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十三·漕运下》,《魏源全集》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594页。
[15]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商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5-896页。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同治元年六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13页。
[17]包世臣撰,李星校:《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11-12页。
[18]胡家鼎:《上海为海疆门户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7《户政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30页。
[19]《两江总督勒保奏陈会查海运情形事》(嘉庆十六年闰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215-056。奏疏收入《清仁宗实录》卷240,嘉庆十六年三月己未,《清实录》第31册,第239-240页。
[20]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0《户政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1071页。
[21]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十三·漕运下》,《魏源全集》第15册,第609页。
[22]《清宣宗实录》卷79,道光五年二月癸亥,《清实录》第34册,第271页。
[23]雍正《大清会典》卷139《兵部·海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4年,第8759页。
[24]道光《厦门志》卷3《兵制考》,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5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87页。
[25]雍正《宁波府志》卷15《兵制·海防》,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999页。
[26] [清]喀尔吉善:《请定巡洋会哨之法以重海防疏》,《皇清奏议》卷4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第397页。
[27]《浙江黄岩镇总兵刘文敏恭报春季巡洋会哨海疆宁谧情形》(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朱批奏折,档号:403056827。
[28]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
[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66-867页。
[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乙巳,第1238-1239页。
[3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2,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庚寅,第2433页。
[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3,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巳,第2474-2475页。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丁酉,第732-733页。
[34]《清宣宗实录》卷360,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壬寅,《清实录》第38册,第501-502页。
[35]据方堃研究,清代“海疆”的空间范围,主要指的是“沿海陆域与部分近岸水域及岛屿”,而不仅仅是近海海域。参见方堃:《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甲午,第1201页。
[37] [清]陈良弼:《水师辑要·七省海疆总论》,《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0册,第395页。
[38]徐家干:《洋防说略·防海说》,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第3a页。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2,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庚寅,第2432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3,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巳,第2474-2475页。
[41]《清宣宗实录》卷384,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己酉,《清实录》第38册,第912页。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丙戌、辛丑,第2523、2545页。
[43]《清宣宗实录》卷460,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庚申,《清实录》第39册,第813页。
[44]《清文宗实录》卷21,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戊戌,《清实录》第40册,第305-306页。
[45]《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查明师船赴北捕盗放洋日期(附片:奏英夷欲令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奉谕饬令追回事)》(咸丰五年八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朱批奏折,档号:406006541。
[46]《漕运总督邵灿奏为抵苏体察情形新漕海运宜守北洋岛屿并捐雇网梢船只捕盗护漕恭折奏鉴事》(咸丰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朱批奏折,档号:406006769。
[47]《清文宗实录》卷179,咸丰五年十月乙未,《清实录》第42册,第1002页。
[48]李鸿章:《请催海防经费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第9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4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72,咸丰十年正月壬戌、己巳,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76、2692页。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6,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庚午、同治元年五月戊戌,第90、248页。
[51]同治九年(1870),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因处置“天津教案”不力被撤职,负责查办此案的工部尚书毛昶熙认为“北洋三口”海防“尤关紧要”,应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将“北洋”洋务、海防责成直隶总督李鸿章全权办理,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获准。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同治九年九月己卯,第3117-3118页。
[52]这一观点以郭卫东为代表,参见郭卫东:《释“北洋”》,《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
[5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同治六年十二月乙酉,第2265-2266页。
[54]曾国藩:《曾国藩书札》卷33《复丁雨生中丞》,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609页。
[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癸卯,第3989页。
[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同治十三年九月丙戌,第3952页。
[57]丁日昌在此疏中未提及奉天海疆,疑为疏漏。
[5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同治十三年十月庚辰,第3957-3958页。
[5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同治十三年十月壬午,第3960页。
[6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100,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癸卯、庚戌、辛亥、癸丑,第4004、4011、4033、4039-4040页。
[6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癸卯,第3987-3992页。
[62]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议筹办海防折(附清单一)》(光绪元年四月),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第6册,第298页。
[63]《清德宗实录》卷8,光绪元年四月壬辰,《清实录》第52册,第177-178页。
[64]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谢恩折》(光绪元年五月初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第6册,第304页。
[6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5,同治十三年六月己卯,第3796页。
[66]李经邦:《防海防陆难易缓急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3《兵政九》,第802页。
[67]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7《原拨海防经费现拟照案仍行分解南洋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1397页。
[68]易顺鼎:《盾墨拾余》卷1《奏疏·敬陈管见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76册,第366页。
[69]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6《请拨海防经费折》,《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07册,第270页。
[70]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12《筹办海防折》,《续修四库全书》第509册,第348-349页。
[71]曾国荃:《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8《洋务八》,第2907页。
[72]《清德宗实录》卷185、189,光绪十年闰五月癸丑、七月己酉,《清实录》第54册,第587、653页。
[73]《清德宗实录》卷215,光绪十一年九月庚子,《清实录》第54册,第1023页。
[74]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51《遵呈海防图说折》,《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07册,第662页。
[75]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66《淮军报销折》,《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08册,第340页。
[76]清海军衙门:《北洋海军章程·简阅》,光绪十四年(1888)石印书局石印本,第1b-3a页。
[77]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9《十四日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79册,第226页。
[78]郑观应:《增订盛世危言新编》卷9《强兵二·海防上》,《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53册,第416页。
[79]郑观应:《增订盛世危言新编》卷8《强兵一·水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53册,第411页。
[80]陈虬撰、胡珠生编:《陈虬集》卷2《筹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3-54页。
[81]《宣统政纪》卷11,宣统元年三月庚午,《清实录》第60册,第230页。
[82]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卷3《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61页。
[83]《清德宗实录》卷442,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辛卯,《清实录》第57册,第825页。
[8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7《兵考二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9733页。
[85]《清德宗实录》卷540,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己巳,《清实录》第59册,第182页。
[86]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8《电报四十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73册,第61页。
[87] [清]陈良弼:《水师辑要·京师二东海图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0册,第393页。
[88]程含章:《复林若洲言时务书》,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12《治体六》,《魏源全集》第13册,第523页。
[89]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7《密陈海口防务暨筹备北路情形折》,《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09册,第224页。
[90]丁日昌:《海防要览·海防条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69册,第106页。
[91]薛福成:《庸庵文编·外编》卷1《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62册,第187页。
[92]丁日昌:《海防要览·海防条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69册,第106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学术研究》,国内邮发代号:46-64,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学术研究杂志社门户网站:中国(南方)学术网http://www.southacademic.com,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手机版 | 归档 | 关于我们| (粤ICP备14048290号 )
主办: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B座7楼学术研究杂志社
邮编:510635
© 学术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