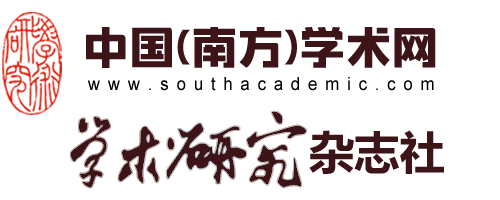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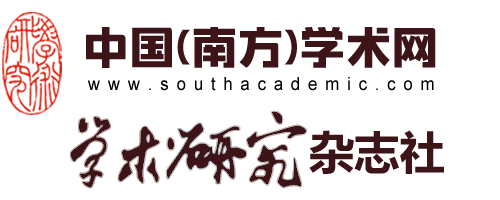
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中国佛教文学存在南北差异。以10至12世纪北宋与辽为例,这种差异大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北方佛教文学长于散文,南方则以诗偈见称;二、北方偏重于表现民间群体的宗教信仰,南方则偏重于传达个体的修行感悟和宗教思想;三、北方总体呈现出清华、质实的风格,南方则更显清丽、灵动。南北佛教文学都是佛教精神烛照下的文学书写,二者本同而末异,很多时段甚至还呈现出融合、会通之势。但是,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空间维度建构南北佛教文学谱系,有助于改变百年佛教文学研究中“重南轻北”的倾向,使众多佛教文献在各自所属的谱系中重新焕发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南北佛教文学 差异 宋 辽 文学谱系
传统观念中的南北之分,不仅缘于山川、水土、气候、风俗的差异,更与中国古代多次出现的南北对峙的政局相关。佛教是外来宗教,所及之处必得融入彼地民风、政治、文化,方有立足之可能,因此,佛教史上南北区分的意识浓厚。汤用彤述及魏晋之后佛教史曰:“自后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对立,而佛教亦且南北各异其趣。于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1]历朝佛教文学的发展,既与佛教盛衰相表里,又势必受彼时彼地文学风尚的影响。前贤对中国文学南北之差异多有论考,但关于南北佛教文学的差异,则罕见述及。本文尝试以10至12世纪北宋与辽对峙时期的佛教文学为例管窥此一问题,理据有二。其一,陈寅恪云:“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2]太虚法师亦云:“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3]佛禅的此种发展态势反映在佛教文学上,便是诸体皆备,臻至极盛。而辽几乎全民信佛,以至于后世有“辽以释废”之说,今存辽朝文学文献,更泰半关涉佛教。其二,宋、辽虽仍存有诸多互通渠道,但隔绝、对抗更是基调;辽朝曾颁布严厉书禁,“传入中国者法皆死”,[4]客观上阻绝了文化流通,及其国覆亡,契丹文字几无识者,此尤可表明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足文化圈之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宋、辽分界大致以11世纪初澶渊之盟议定的白沟河(今河北中部、山西东部)一带为限,与通常认定的以秦岭、淮河为标志的南北分界线尚存一定距离。然而,南北之分不惟地缘之观念,更属政治、文化之范畴,实不必太过谨守地理图志。
一、南北佛教文学的文体
佛教文学的文体,就其来源看,无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土固有的文体这一“旧瓶”装新酒,像诗歌、碑文、铭文、记文等,其文体规范、功用与世俗同类文体几无大异,只不过内容是宣传佛教义理和精神而已;二是应自身发展需要而衍生的新文体,例如,以韵文说教的偈颂,虽约略相当于中土的颂,但实为印度舶来的文体,而诸多纷繁复杂的佛教科仪,像水陆法会、斋戒、忏仪等,亦催生出相应的法会文、斋文、忏文、启请等仪轨文,此为佛教文学对中国文体学的独特贡献。
文体虽属形而下层次,但又是“有意味的形式”。它的产生、演变、定型是人们长期探索、反复演练的结果,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不同时期、地域、民族的作家在抒情达志、记人叙事时,对文体的选择往往有着特殊的偏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思维和审美倾向。南北佛教文学之差异,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文体,这在五、六世纪南北朝对峙时即已显现出来。北朝佛教文学,发端于北魏,自其伊始,在文体上即以散文为主,诗偈则几无所闻。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40名释氏“本土之谣” 86首,绝大多数出自南方僧侣,惟山西、陕西各有1人。然而,北朝佛教建塔、立碑、造像的风气极盛,留有众多的造像记、碑记、塔记等佛教散文,清人王昶《金石萃编》云:“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造像必有记(记后或有铭颂),记后题名。”[5]王昶虽是综论佛教造像之发展,但针对的主要是北朝。
北方佛教文学长于碑铭、记文等文类的特征,相沿至辽。翻检《全辽文》,触目皆是信众、僧徒所撰佛教经序、碑铭、颂赞、塔记、幢记、题记、杂著等文类。譬如“幢记”,《全辽文》收有65篇,仅次于“诏谕”(137篇)、“墓志”(84篇)。幢记是指勒于幢体上的文字,用以记述造幢之缘起、意图、经过,盛行于唐开元之后,与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衍关系甚大。辽人建幢之风尤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莫不乐于兹事。正如有学者所说:“历朝历代建造石幢者,以辽朝为最。”[6]从某种意义上说,幢记堪称辽朝最具特色的文体。此外,《全辽文》还收有49篇塔记文,是辽朝佛教文学的另一大文类。辽人笃信佛塔的神秘功能,相率造塔,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他们在佛塔之上,亦撰文勒石,以志其事,故塔记文颇为繁复。但是,辽朝佛教诗歌却显得非常贫乏。《全辽金诗》共收辽诗“率不过百余首”,[7]其中僧人所作10题,文人及无名氏所作佛教诗歌7题。在这些佛教诗歌中,《醉义歌》是辽代最长的诗歌;“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则是目前所见辽代规模最大的同题集咏,不过,其艺术价值不足称道。
与北方佛教文学不同的是,南方佛教文学则以诗歌、偈颂等韵文见称。自东晋以迄北宋,中土能诗的释子甚众,但保守估计有八成以上皆出自南方。我们根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8]录得唐代占籍可考的释氏诗人共119人,其中福建28人、浙江26人、江苏9人、江西7人、四川7人、广东4人、湖北3人、湖南3人,共87人,占总数70%以上。后世用以特指“以诗鸣世”的释子的术语——“诗僧”一词的出现,亦与南方僧侣相关。刘禹锡曰:“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9]灵一、护国、清江等人皆是大历年间蜚声江南诗坛的释子。北宋释子继承了南方释子善诗的传统,更为注重诗偈的写作。据成明明统计,《全宋诗》第1至23册,收录北宋诗僧总计344人,占籍可考者207人,北方的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总共仅19人,其余皆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10]北宋释子之诗,影响甚著。宋初九僧诗,规抚晚唐,号为“九僧体”,乃宋诗一大“家数”。北宋释子还多有别集行世,像《九僧集》《石门文字禅》《参寥子诗集》等,实可颉颃于文人别集。陈师道赞释道潜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11]四库馆臣评惠洪《石门文字禅》曰:“其诗边幅虽狭,而清新有致,出入于苏、黄之间,时时近似,在元祐、熙宁诸人后,亦挺然有以自立。”[12]北宋释子之诗还引起苏轼、叶梦得等诗评家广泛关注,他们发明了“蔬笋气”“酸馅气”“菜气”等术语特指僧诗风格。职是之故,四库馆臣得出一个印象:“以宋代释子而论,则‘九僧’以下,大抵有诗而无文。”[13]同时,北宋文人多信仰佛教,与僧人交往愈加频繁,也创作了大量的涉佛诗偈。例如,与佛门结有深厚因缘的苏轼,频游寺院,光游寺诗即达220余题,故苏辙有诗云:“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14]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皆效寒山等僧人诗偈,援禅入诗,以诗释禅,传达理趣。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所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翻案法”的创作手法,与佛禅亦有密切关系,故金人刘迎诗云:“名高冀北无全马,诗到西江别是禅。”[15]可以说,佛教诗偈不仅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推助了宋诗风貌的形成。另外,北宋涉佛散文颇为繁复,凡寺院碑记、幢记、塔记、塔铭、榜疏、愿文、忏文诸体皆备。据统计,北宋的佛寺文约有1200余篇,其中80余名僧人参与创作了200余篇。这里的佛寺文,是指以“佛寺或者佛寺内的代表建筑(如法堂、讲院、钟楼、塔等)名篇的,或者以佛寺风光物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章。从文体上来说,包括记、碑、铭、赞、序、赋、箴、传、题名、榜、疏等多种文体”。[16]佛寺文虽未涵括所有涉佛散文,却为其主体部分,足可说明问题。这1200余篇佛寺文在总共10万余篇的宋代散文中所占分量,明显不如同类文体在《全辽文》中的地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的意义亦远不如诗偈。
二、南北佛教文学之旨趣
佛教文学是指宣传佛教教义、教规、精神,反映信众宗教实践的文学。不过,因佛教派别、文化习尚、文体规范等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佛教文学的旨趣有所偏重:或者直接宣传演绎教义,或者通过记人叙事阐扬佛禅精神,或者传达信众个体的修行体验。例如,五、六世纪的南北朝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忏悔文,但各自的旨趣有别:北朝的忏悔文主要因袭了《佛说决定毗尼经》中的“忏悔文”,程式化非常明显;南朝的忏悔文则主要出自梁武帝、江总、沈约、陈文帝等人之手,不仅所据佛典更加丰富,而且文辞典雅,呈现出独特个性和思想性。[17]南北佛教文学文体既殊,旨趣亦别,大抵而言,北方长于叙事以宣传教义,偏重于表现民间群体的宗教信仰;南方则长于抒情发志,偏重于传达个体的修行感悟和宗教思想。
佛教散文中数量众多的碑铭、记文、塔铭等文类,通常是以记人叙事的方式彰显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其目的“盖所以备不忘”。这类文体明显存在固定的写作程序,一般都是先记述建寺、构塔、造幢之机缘,铺叙构建者或塔主的生平,再则旌表其功德,祈求福报。同时,它们的用语也很相似,像辽朝盛行的幢记文,反复出现“尘沾影覆”“拯济幽明”等用语,其祈愿词上及国家君王,下及父子昆弟,往往不出“礼赞帝后”“万民乐业”“阴翊子孙”“解厄度脱”“同沾利乐”等目的。这些用语明显是脱化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世尊的教导,竭力赞颂尊胜陀罗尼的“灭罪与度亡”“禳灾与祈福”“报恩与尽孝”等方面的强大宗教功能,[18]而很少阐释精深的义理。南方佛教散文基本遵循着特定的文体规范,亦以叙事为主,但相对辽朝而言,叙事之余经常传达作者的心性体验,抒写对事理的感悟,赋予了更多的个人色彩。例如,释契嵩《漳州崇福禅院千佛阁记》先是叙述显微长老建阁的机缘、经过,描写千佛阁之“陵空跨虚,飞桥危亭,骞涌旁出”的形制规模,然后用儒家圣人垂象成德的观念,阐发创立佛阁的意义。又如,欧阳修《明因大师塔记》先叙写明因大师的生平,继而以大段文字讨论明因大师家乡太原的民风沿革。再如,苏轼著名的《黄州安国寺记》,主要叙写自己被贬经过以及在寺中“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的情形,仅在末篇寥寥数笔提及安国寺的沿流,虽名为“寺记”,实质则是书写心曲、痛自省察的独白。这样的佛教散文,明显不同于通篇皆记事志人、发愿祈福的辽朝佛教记文。总之,北方佛教散文书写的重心是信众对于佛教的虔敬之情,他们似乎从不怀疑佛教的强大、神秘功效,甚至无意追究其真实内涵,只是表达自身的狂热之情;而南方佛教散文在记人叙事时,常常以儒家思想考量佛教的本质或反映自己的心境,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太虚大师曾将宗教分为鬼灵教、天神教、自心教,所谓“自心教”,即“认定惟是自心之心境,否认种种鬼灵及惟一无二能造作主宰宇宙万有的造作主宰者”。[19]依据这种分法,北方佛教文学体现的更近似于“天神教”,而南方佛教文学体现的则是一种“自心教”。
南北佛教文学旨趣之不同,还体现在诗偈的写作上。辽朝的佛教偈颂,多为无名僧人所作,外示鄙俗之貌,内藏警示之义,跌宕骇俗,以白描、叙述、议论为主要表现方式,或表现对地狱恶道的畏惧,对西方净土世界的向往;或批判世人名利之心,宣传佛教因果报应论。例如,《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收录的《诸经偈语(十二则)》后三首:“城外一所土馒头,馅草都是人骨头。各人吃一所,有甚没来由。”(十)“奸汉谩呆汉,呆汉又不呆。奸汉作驴儿,却被呆汉骑。”(十一)“若人成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十二)[20]这些诗偈,估计是抄经者即兴摘抄、创作而成,或比类经义,或藉以引申,阐发事理,语言通俗晓畅。我们知道,白话诗偈最早出现在佛经当中,南朝释亡名继而作之,唐代王梵志、寒山更因此而名显,特别是王梵志诗长期流传于西北边陲,应县木塔出土的这些诗偈,很可能就受其影响。例如第十首,明显从王梵志《城外土馒头》一诗改作而来,只是稍微变动了句式和用语。北宋的佛教诗歌则呈现出迥异的旨趣,更注重传达个体的宗教体验,题材明显表现出山林化和哲理化的倾向。[21]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载九僧作诗不出“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22]虽语含戏谑,却反映出北宋僧诗题材狭仄的普遍倾向。北宋释子藉山林风物,一方面抒写幽深清远、洒然尘外的林下风致,像道潜、惠洪的诗歌;另一方面则阐发一种诗化的哲理,像永明延寿《永明山居诗》,在感悟自然万物同时,传达出瞬刻永恒、幽远玄奥的哲理。北宋丛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宗纲偈、传法偈、开悟偈、临终偈等禅门偈颂。这类禅偈又称为“文字禅”,或者阐释晦涩难懂的佛教名相、义理,或者营构清新圆融的禅境,或者传达禅人者对禅境、生命、宇宙万有的感悟,整体呈现出浓郁的诗化色彩。兹举天童正觉关于“药山升座”公案的颂古为例:“痴儿刻意止啼钱,良驷追风顾影鞭。云扫长空巢月鹤,寒清入骨不成眠。”[23]“药山升座”是禅林盛行的公案,较早出现在《祖堂集》卷四,大致是说,药山惟严禅师久不升座说法,院主参请,药山令打钟集众,药山升座,良久,不垂一言,便下座,归方丈。所谓“不垂一言”,原是禅门高妙法门,所谓语默静处,扬眉瞬目,莫不举全体之性。天童的颂古前两句用“黄叶止啼”和“外道问佛”两个典故,阐明药山禅师“不垂一言”,实与世尊说法如出一辙,超越了有无相对之境,了无纤尘可染;后两句用“晴巢月鹤”“清不成眠”两个意象,象征佛法在心,惟心体清净,自足圆满,何假外求的道理。这类禅偈明显不同于辽朝那些用以警醒世人的白话偈颂,而更具有哲学意味和诗性色彩。
宋、辽偈颂呈现出的不同旨趣,与各自的佛教发展格局密切相关。辽朝佛教义学发达,宗派林立,华严、密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盛行于北宋的禅宗却影响微渺,甚至还一度遭到压制。高丽义天《飞山别传议跋》描述辽境禁禅的情形:“甚矣!古禅之与今禅,名实相辽也。古之所谓禅者,藉教习禅者也;今之所谓禅者,离教说禅者也。说禅者执其名而遗其实,习禅者因其诠而得其旨。……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除其伪妄。”[24]就精神旨趣、传释方法、修持方式而言,禅宗无疑是中国佛教诸宗中最接近诗歌艺术的宗派,但是它在辽境却极度式微,这应当是辽朝佛教文学总体缺乏诗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南北佛教文学之风格
南北佛教文学风格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体而言,北方佛教文学清华、质实,南方佛教文学则更显清丽、灵动。
前人常以“浅陋”“鄙俚”评价北朝的造像记、佛寺碑,例如,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六认为,北魏造像“文字率欠雅驯”。[25]赵绍祖《金石文钞》凡例亦云:“凿佛造像语言鄙俚者,如北魏龙门、唐岱岳观之类。”[26]《全辽文》中收录的很多造经题记、石函记等,都极简略地记载了捐刻者、校勘者、讲经者的姓名、阶衔,质木无文,因此,叶昌炽评曰:“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潦草者如市中计簿,满幅题名,皆某儿、某郎妇之类,北伧乔野之风于此可见。”[27]叶氏的说法,虽语含轻视,但代表了多数初涉辽代文献者的印象。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自北朝以来,很多北方佛教散文其实是骈散结合,大段使用四六文,形式上较南方更追求工丽。著名的《洛阳伽蓝记》即被后世誉为“妙笔葩芬,奇思清峙”,[28]这与北魏“综采繁缛,兴属清华”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辽朝的佛教散文也大抵承续了此种风格,例如,李翊所撰《特建尊胜陀罗尼幢记》开篇云:“伏闻护明下降,爰欲度于四生;调御出兴,遂震摇于六种。恒施慈念,广运悲心,示方便于三乘,发弘誓于四愿。教之惠施,作苦海之津梁;化以归依,指迷途之径路。比为常弘释梵,永济人天,迁神忽现于缘周,示迹故留于遗法。遂有封祑于堂殿,或乃刊勒于碑幢,讽之者福不唐捐,诵之者功超远劫。若乃轻埃霑处,微影覆时,非惟获果于未来,兼亦除殃于过去者,莫若佛顶尊胜陀罗尼矣!”[29]这段文字辞义清铄,揄扬发藻,既有赋体的铺陈气势,又具骈文的整饬华美,很难用“鄙俚”“欠雅驯”评之。这样的文字在辽朝佛教散文中颇为常见。它们与南方佛教散文相比,缺乏的不是形式美、文采美,而是自然美和灵动感。像释了洙《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中的一段写景文字,尤能说明问题:“春阳方煦,层冰始泮,异花灵药,馥烈芬披,溪谷生云,林薄发吹。夏无毒暑,在处清凉,怪石颟顸,矗莎叠藓,谈道之者,匡坐其上,横经挥麈,议论譊譊,奇兽珍禽,驯狎不惊。秋夕云霁,露寒气肃,岩岫泊烟,松阴镂月,猿声断续,萤光明灭。□崖结溜,冬雪不飞,长风吼木,居实凛然,一径东指,旁无枝岐。”[30]这段文字主要描写丰山四时之景,皆为齐整的四言,文辞丰赡华美,但仔细味之,它更像是堆砌而成,随意增删皆可成文,此正如叶昌炽所说“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
北宋的佛教散文虽亦以叙事为主,但多以散体行之,又常藉事阐发哲理或传达心性,故而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例如,惠洪《待月堂序》,叙写建堂经过的文字极为简略,更多地是描写他和真教禅师游观之乐:“堂临晴湖,日光下彻,俯见游鱼,聚立纵望,湘西山云之纤秾,草木之深密,一览而尽得之。真教拊栏哦曰:‘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而今却向山边去,只有湖水无行路。’”[31]对比上引释了洙的景物描写,惠洪的文字更显轻灵,所以四库馆臣以“轻而秀”评价他的文章。再如,黄庭坚《幽芳亭记》,记方广院中的幽芳亭,几无一语涉及其渊源,而是围绕“兰”作文,讨论“兰香从甚处来”:“若道香从兰出,无风时又却与萱草不殊;若道香从风生,何故风吹萱草无香可发?若道鼻根妄想,无兰无风,又妄想不成。若是三和合生,俗气不除。若是非兰非风非鼻,惟心所现,未梦见祖师脚根有似恁么,如何得平稳安乐去?涪翁不惜眉毛,为诸人点破:兰是山中香草,移来方广院中。方广老人作亭,要东行西去,涪翁名曰幽芳,与他着些光彩。此事彻底道尽也,诸人还信得及否?若也不得,更待弥勒下生。”[32]这段文字直如禅家语,跳脱潇洒,机趣纵横,此种风格在北方佛寺文中是绝难见到的。北宋佛教散文呈现出迥异于辽朝的风貌,与当时诗文革新运动摈弃繁缛文风,追求平易、自然之文,密不可分。
南北佛教诗歌风格的差异更为明显。辽朝文学多出于“释子、村学究”,他们的才情和文采,难以媲美文人学士。海山思孝是辽朝文化水平最高的佛教作家之一,早年曾举进士第,著有《海山文集》行世,但今所见《和兴宗诗二首》《天安节题松鹤图》,风格质实直白。再如,寿昌五年(1099)沙门智化倡导的玉石观音像唱和,共有二十四位释子和文士参与,歌咏的对象是智化费时三年所造的石像观音,构思、风格几乎如出一手,兴象粗疏、贫弱。北宋佛教诗歌风格比辽朝更显丰富,总体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文人化的倾向。例如道潜之诗,晁公武评曰:“其诗清丽,不类浮屠语。”[33]惠洪也说:“道潜作诗,追法渊明。”[34]都指出了道潜诗歌文人化的倾向。而惠洪本人的创作,也常被指为不类浮屠,例如,陈振孙谓:“其文俊伟,不类浮屠语。”[35]北宋佛教诗歌甚至还常以绮语入诗,表现相应的佛理、禅趣,例如,陈衍评惠洪“异在为僧而常作艳体诗”。[36]这种情形在辽朝佛教文学中很少见到。二是僧人特有的风格——“蔬笋气”和“酸馅气”。这类诗歌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苦吟诗风,具有题材狭窄、边幅短狭、多摄禅语、境界清寒等特征。例如,姚勉评真一上人诗谓有“蔬笋气”:“真诗入清绝处,如风松韵涧,月鹤唳皋;写荒寂处,如宿雁秋芦,寒鸦晩日。益进不已,岛可直异时同调也。”[37]
宋、辽的偈颂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例如,前面所举《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收录的《诸经偈语》,因为接受者往往是普通信众,所以常常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表达方式,警示世人。而北宋偈颂因为多表达个人修行感悟和对佛禅义理的理解,又因为佛禅历来形成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统,所以他们在诠释禅理、禅意时,常常以自然意象为媒介,运用象征、联想、隐喻等手法,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例如,曹洞宗的宗纲诗,为阐明曹洞正偏回互宗旨,在选择山水意象时,即用“灵源、皓月、寒岩、青山、流水、岩谷、孤峰顶上”象征正体,与之对应的则用“支派、轻烟、薄雾、白云、波浪、市廛、十字街头”象征偏体,通过这些意象的交互关系,象征理与事、本体与事相、空与色、静与动五种不同的关系,进而阐明修行的进阶。[38]
四、建构南北佛教文学谱系的意义
南北佛教文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在形态、表现旨趣、呈现方式上的不同,而其根本皆是佛教文化精神烛照下的文学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实“本同而末异”。同时,南北文化犹如南北政局,既有疏离的状态,亦有会通之时。宋、辽对峙中的南北佛教文学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是因为此一时期瓜剖豆分,南北文化圈相对更显封闭。然而,当南北文化圈相对开放之时,特别是大一统之时,这种差异可能就比较模糊。宋、辽对峙之后,紧接着是宋、金对峙,南北分界南移,融合趋势愈加明显。金人废除了辽朝的书禁,文献渐开,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辛弃疾等人的诗文集流播于北方。很多北方僧侣南下避难,南方僧侣亦因诸种机缘而北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一载,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人来索详通经教德行僧,开封府即令拘诸禅院僧等,每院不下十余人,解赴金国,军前复有退令归者,所留仅二十人,待遇颇厚。诸寨轮请斋供,殆无虚日”。[39]曹洞宗青州希辩、临济宗教亨虚明、云门宗佛觉宗赜等僧人,皆自南北上,传本宗家法,使曹洞、临济、云门诸宗在北方蔚然兴盛,逐渐改变了辽朝佛教以义学为主的特质。例如偈颂体的写作,金代僧侣创作的主要是开示偈、悟道偈、传法偈、辞世偈、宗纲偈,而非警示世人的白话偈颂,像曹洞宗普照希辨、大明僧宝、王山体、雪岩如满等人都曾用诗偈的形式阐述“正偏五位”本宗家法,万松行秀更仿照圆悟克勤《碧岩录》,撰有著名的颂古评唱《从容录》和《请益录》。金代佛教文学的发展状况,体现出了佛教文学由南渐北的趋同之势。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虽波澜起伏,历经艰辛,却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和成绩。与之相呼应的是,当前正积极推进的两种《中国佛教文学史》的编撰工作,[40]适足反映了学术界对全面梳理佛教文学史实、建构佛教文学谱系的良好愿望。文学谱系的建构,其要义在于考镜源流、辨章体制、核定品位。但是,文学的历史生态本身丰富多样,流动不居,因此文学谱系不应只是“单一的线性链条”,而是由多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型结构,既包括历时性的纵向梳理,亦应涵括共时性的横向研究。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理念,或以作家为中心,或以文体中心,或以空间为中心,或以观念中心,常常会建构出不同形态的文学谱系。鉴于中国佛教文学客观存在的南北差异,我们认为有必要重视空间的维度,构建南北佛教文学两个不同的谱系。
首先,建构南北佛教文学谱系,是基于文献存留状况考虑的。大致来说,南方佛教文学文献基本以书籍为载体,多见于集部以及僧传、语录之中,流传有序;而北方佛教文学文献率皆藉碑刻、抄卷而存,残章断简,漫漶不清,撰者的生平也大多无考。比如,耶律楚材据契丹语翻译的寺公大师《醉义歌》,所呈现的情韵、质感、风格都明显异于其他辽诗,故耶律楚材惊叹为“不类人间语”。这明显是一种誉词,因为汉语诗歌中并不乏类似的作品,他更应诧异的是:作为一个契丹诗人,寺公大师何以能写出如此纯熟的长篇歌行?然而,我们所知“寺公大师”的信息,只有耶律楚材译序中寥寥数语:“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41]尽管有学者从南北文化交流、社会背景等方面探讨寺公大师的身份归属和创作渊源,[42]但我们的直觉是,契丹的文化土壤是不太可能培育出这样的诗歌的,它之所以在辽诗中“异峰突起”,可能与耶律楚材的翻译之功密不可分。因此,就辽代佛教诗歌而言,我们能够获得的仅仅是一些断续无痕“知识碎片”。面对着这些“知识碎片”,谱系学的方法不是寻求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律,而更注重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和不连续。因为它们本身就存在于充满断层和裂缝的历史之中,人为弥合这种断层、裂缝,实际上是一种权利意志的体现。对此,我们只需要做“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43]而试图“找到一个绝对的起始或本源”,是不太可能的。[44]与之不同的是,南方佛教文学文献丰富,作者、系年、流衍大多有序可考,运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不仅可以揭示出作者的教派归属,甚至可以厘清他们的创作源流。
其次,按照福柯的观点,谱系学方法是用来书写“问题化历史的”。知识谱系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问题意识的差异,某种谱系中的核心问题,在其他谱系中则可能变得无足轻重。例如,北方佛教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功利色彩极强的祈愿词,常被一些正统儒士轻视,但这实际上是北方佛教文学的核心问题。北方佛教“重在宗教行为”,诵经、建幢、立像、布施、祈愿几乎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自发成立了一种独特的民间组织——邑社,规模常达上千人以上,称为“千人邑”。像邑社成员这样量力集资,念经奉佛,襄办佛事,看似“鄙俚不经”,却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王昶曾论曰:“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伤离乱而想太平,迫于不得已,而不暇计其妄诞者。仁人君子阅此,所当恻然念之,不应遽为斥詈也。”[45]王昶将这种愿望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自属“同情之论”,但无论贤愚贵贱皆怀此种愿望,这可能就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是一种族群普遍性格和信仰。契丹原属游牧部落,从其兴起到统治北方地区,时间不过二百余年,很多方面仍未能摆脱低级形态的社会属性,其人剽悍善战,简单朴质,部族、群体意识十分强烈,在这种意识的强大吸附力作用下,个体民众的心灵和活动总是遵循着种族或群体的模式,所以佛教之于辽朝,几乎是达到了“全国化”“全民化”的程度。反观南方的佛教文学,当然也有类似的祈愿词,但不属于核心问题。南方佛教“偏尚玄学义理”,书写的重心往往是信众的禅悦风致和幽玄微渺之思,而不是这种功利性极强的祝祷、祈愿之情。南方同样也出现佛教社团,性质却与北方有所差异。中土的佛教社团盖始于六朝。东晋慧远集文士、释徒于庐山东林寺栖心念佛,共期西方净土而结“莲社”;北魏则出现了在家信徒以营造佛像寺塔为机缘的“义邑”。“莲社”走的是文化精英的道路,除了念佛咏经,谈禅证道外,还经常诗文酬答;而“义邑”则重在发展底层民间的信众,通过行香诵经、襄助佛事,积累善业,以求果报。“莲社”和“义邑”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佛教社团,在南方、北方分途发展,特别是北方地区几乎都沿袭了“义邑”的模式。如果将南北佛教文学置于各自的谱系中加以讨论,它们各自的价值恐怕就不能彼此轩轾。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很多北方佛教文献(特别是南北对峙时期)往往被认为缺乏“文学性”,只是作为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的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很少被文学研究者关注。百余年的佛教文学研究隐然存在“重南轻北”的倾向。如果我们采纳传统的“泛文学观”,摒弃西方狭义的“文学”观念,消解“文学性”至上的影响,那么,很多佛教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在各自所属的谱系中可能会重新得到彰显。
总之,建构南北佛教文学谱系,是基于文献存留状况及其自身性质而考虑的。相对于“单一的线性链条”型的谱系形态,这种空间维度的文学谱系实质是将一些“知识碎片”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力图揭示出“各种不同的能量在互相对话或较量的过程中刻写在文本中的意义的痕迹”。[46]需要指出的是,从谱系学的角度强调南北佛教的差异,并非有意割裂二者的关联。正如前面所说,佛教文学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实“本同末异”,它们之间的交流、融合亦从未中断,因此,作为佛教文学谱系之下的两个子系统,南北佛教文学谱系同样存在很多重叠、交合之处。
注释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5页。
[2]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3]太虚法师:《黄梅在佛教史上之地位及此后地方人士之责任》,《太虚大师全书》第26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5年,第108页。
[4] [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卷十五,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13页。
[5] [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712页下—713页上。
[6]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71页。
[7] 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页。
[8] 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8-170页。
[9]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40页。
[10] 成明明:《北宋诗僧研究》,扬州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11] [宋]陈师道:《送参寥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1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石门文字禅》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1页。
[1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北磵集》提要”,第1405页。
[14] [宋]苏辙:《栾城集》卷十三《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15] [金]刘迎:《题吴彦高诗集后》,[金]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03页。
[16] 李晓红:《北宋佛寺文研究》,山东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17] 王飞朋:《南朝佛教忏悔文考论》,《三峡论坛》2015年第1期。
[18] 张国庆:《辽代经幢及其宗教功能:以石刻资料为中心》,《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19] 太虚法师:《我之宗教观》,《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第224页。
[20] 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第93-94页。
[21]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269页。
[22]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6页。
[23] [宋]万松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231页下。
[24] [宋]宗鉴:《释门正统》卷八,《卍续藏经》第1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902页。
[25] 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26] [清]赵绍祖:《金石文钞》凡例,清光绪二年重刊本。
[27] [清]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卷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28]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4页。
[29] [辽]李翊:《特建尊胜陀罗尼幢记》,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5页。
[30] [辽]释了洙:《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70-271页。
[31] [宋]释惠洪:《待月堂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0册,第270页。
[32] [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3页。
[33]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49页。
[34]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4页。
[35]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
[36]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37] [宋]姚勉:《姚勉集》卷四一《题真上人诗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0页。
[38] 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6页。
[39]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0页下。
[40] 分别是:张弘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共8卷;吴光正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其中《中国佛教文学史》共11卷。
[41] [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1页。
[42] 陈重、米有华:《试谈辽代长诗〈醉义歌〉》,《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
[43]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44] [美]加里·夏皮罗:《翻译、重复、命名——福柯、德里达与〈道德的谱系〉》,萧莎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第345页。
[45] [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三十九,第713页上。
[46] 张德明:《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1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学术研究》,国内邮发代号:46-64,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学术研究杂志社门户网站:中国(南方)学术网http://www.southacademic.com,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手机版 | 归档 | 关于我们| (粤ICP备14048290号 )
主办: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B座7楼学术研究杂志社
邮编:510635
© 学术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