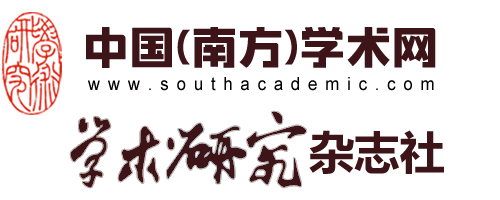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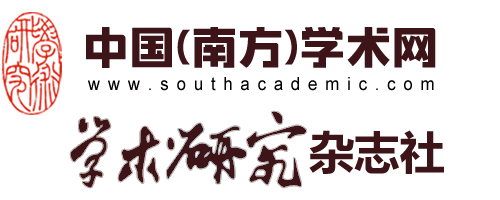
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题之一。现代性的兴起伴随着自我理解与“社会想象”的深刻变迁。一方面受到启蒙运动以降各种现代思潮的观念塑造,一方面受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和技术化等)进程引发的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人”不再注定是相对同质化的有机共同体的成员,生活在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之中,面对着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规范等各方面的“交错压力”,认同问题也由此突出:我们是谁?我们的归属感源自何处又指向哪里?我们的行动的道德意义与规范依据何在?这些问题始终纠缠着现代人的心灵,并造成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多种影响和后果。

我所举行“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22日到2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于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举办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讨论会,旨在于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脉络中,以现代认同问题为中心展开相关研讨。本次会议将继续“现代性之反思”的主题讨论,同时也为促进两岸三地学者(尤其是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同行)之间的合作交流确立了卓有成效的机制,来自中、美、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研究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围绕会议议定主题,与会代表提交了20余篇论文,讨论题目涵盖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哲学,国际政治,集中在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起源与演变),现代国家与政治认同,个人、社会与国家,“天下观”与现代国家,现代认同的世俗性与超越性和现代认同的批判性阐释(或后现代“解构”)等议题上。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刘擎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萧高彦教授分别致辞。在简短的开幕仪式过后,两场研讨报告会即刻开始。
本次研讨会议的开场研讨报告的主题为“传统与现代”。白彤东(复旦大学)首先做题为“恻隐之心、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儒家对现代社会认同问题之回答”的报告,他认为中国虽努力遵循发端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行事逻辑和议事规则,结果却不甚理想。实际上,中国在春秋战国所经历的变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已多有可比之处。中国在周秦之变中天下共主的崩塌与欧洲教权式微类似,其时的国家间关系受到“丛林法则”的支配,而先秦儒家在面对这种变化时,发展出一套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较西方遵循强的(狭义的)民族主义更加平和,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华夏文明的扩张相对和平。同时,这套政治哲学与自由宪政式的民族主义相比,有资源认可和支持相对厚重的国家认同。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则以“新天下主义”为中心,探讨民族国家、天下与现代认同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中存在着的古代-帝国/近代-民族的二分,是一个从欧洲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历史模式。这种分析框架尽管有一定的价值,但亟需一种用中国历史自身的概念理解中国的可能性。宋代以后的中国认同,用中国自身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辩证关系来阐述,更能接近中国历史内在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夷夏之辨发展出刚性的、具有原教旨性格的族群民族主义和柔性、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全人类的文明(也包括中国自身的文明)打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未来的中国认同是一个重构的过程,需要的是敞开的、面向未来的建构性认同——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对普世文明的追求,其普遍主义之“好”应该中西兼容、跨越古今。萧高彦(台湾中央研究院)通过爬梳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建构的“人权清单式自由主义”,在系统建构的基底,存在着一种共和主义式的、以人民的集体行动开端启新的潜流。萧教授指出,虽然张佛泉并没有实际上证成“政治契约”如何可能得到社会成员的全体一致同意,而仅仅做出了一种必当如此的道德预设,但关联到其《自由与人权》,我们可以说他通过人权清单、政治契约、以及宪法的创建,排除了民族主义色彩,一方面完成了以人权为主轴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也为这个自由主义奠定了符合此种形而上学原则的民主共和之政治基础。萧教授希望,由此可以使得人们注意到台湾威权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系统建构中,实际上存在着共和或民主集体创造的政治秩序概念。
本次研讨会议的第二场研讨报告的主题为“文化与价值”。曾国祥(台湾中山大学)在其报告“人性尊严与跨文化之价值认同”中尝试从“人文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和思索西方的道德价值与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与可能出路。他肯定跨文化之间存在着“价值联系”,这种“价值联系”使得“人性尊严”被视为西方世界所提出的“人类共同理解之邀请”,而各个不同的文明则能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这一具有普遍特质的人类价值。他论述了康德对于“人性尊严”的开拓以及查尔斯.泰勒对其的发展与丰富,发现新儒家的“道德内在说”与前述二者皆有特定的呼应和契合之处,而泰勒与儒家学说的“家族相似性”特别引人注目。包括当下国人在内的历史行为者,应从自由主义和儒家汲取资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价值进行理解和判断。蔡英文(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的报告分析了福利国家的规范性论证:若我们接受社会福利国家治理的正当性,我们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性论证去解释此正当性,国家治理的限度在哪里?以这个解释为脉络,蔡教授解释了福利国家所依据的公民"互为义务的合作团结"(solidarity) 的可能性,特別阐明了Rosanvallon 的福利国家理论,强调其理念是福利国家在落实公民的社会权利上必须有所节制。王斑(美国斯坦福大学)遵循葛兰奇的政治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是单薄的,狭义的,而是拥有深远政治意涵的。中国革命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与葛兰奇的政治文化观遥相呼应。以小说家、批评家周立波为例,周立波在延安鲁艺的教学工作,将世界文学引入革命文学,热烈地拥抱欧洲人文主义传统,进而起到了建构民族、推动革命的功用。将自决的启蒙人文主义思想为前提,革命者力图通过结合民族和世界的要素创造革命文化,而这种革命文化兼具“文化的”和“世界的”双重含义。
在两场全员报告研讨会结束之后,与会人员分别参加了主题丰富的八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对“天下”及其衍生出的问题的关注是本次会议的特点之一,主题为“天下与国家”的研讨就集中讨论了与“天下”相涉的诸多问题。赵刚(美国阿克伦大学)的报告主题为“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基于对时下“汉化论”和“新清史”的检讨,他从“大一统”观念出发,在清代多民族帝国形成和早期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对“《象纬考》为何要用经纬度取代分野”、“《舆地考》为何要用‘本朝之制’取代‘九州’模式”和“《四裔考》为何要采用朝贡互市两分的方式记述与中国交往的海外诸国”等三个问题的具体考察,从新的角度检讨了清代多民族帝国形成的历史以及国内仍然盛行的“闭关锁国论”的得失,而且从新的角度探讨了早期全球化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与赵刚教授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不同,任锋(中国人民大学)从政治学角度对历史进行了理论提升,他的报告主题为“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 宪制会话中的现代认同问题”。他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儒家之间围绕现代认同问题展开的讨论,可以放在一种宪制会话的视野中进行良性整合。儒家自身可以生发出一套国族论述,并且为自由民族主义提供支援与批评资源。更重要的是,受儒家文明的天下理念启发,兼顾传统治理智慧与自由根基的旧邦新命还会获得一个超越性的世界主义远景,最终指向对于现代国族弊症的约制与克服。在历史与理论之上,裴自余(华东师范大学)则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他认为,中国传统国家类型或可称之为“天下国家”,一方面古代思想认为“天下”而非“国家”才是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天下”又呈现出以皇帝制度为中心的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基本国家形态。天人相与的宇宙意识构成了这种天下国家的观念基础,“天与人归”是古代政治权力正当性的终极来源。这样一种天下国家具有政治地理和文化社群的多重含义,“天下一家”和“一家天下”,“天下为私”与“天下为公”,共同构成了天下国家的一体两面,与之相伴始终。
法国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思想的重镇。主题为“法国政治思想”的报告研讨对托克维尔、涂尔干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思想作了考察。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透过对托克维尔文本的解读,希望找到民主革命与专制的隐秘关联。她发现托克维尔在解释民主革命何以在美国与法国呈现了迥然相异的面貌时,特别注意中世纪后期绝对王权兴起以来法国政治生活最显著的变化:行政集权——将地方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的扩张。这种扩张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社会自组织能力不断丧失,社会集团之间相互孤立和彼此冷漠,抽象的文人政治出现并发展。上述原因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法国在经历民主革命之后仍然要承受以专制为代表的旧制度余毒,在百余年后才得享民主的积极成果。刘拥华(华东师范大学)在其报告“道德、政治化与空洞的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中阐释了涂尔干思考脉络中的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他指出,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深刻冲突与矛盾被涂尔干刻意回避了:个体因为其作为群体成员资格而具有的道德性,社会也因此得以团结和形成特定的纽带。因此尽管社会分工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世界主义的现实基础,人类仍旧是生活在群体生活之中的,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便是民族国家,离开群体生活,我们不但无法落实世界主义的诉求,更无法使得社会团结起来。然而,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各种认同都在寻求其正当性,这表现为对现存的民族国家的挑战,换言之,因为共同体瓦解了,身份认同才被创造出来。这一系列社会发展进程对涂尔干的理论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崇明(华东师范大学)的在其论文《现代政治中的抽象与认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研究》中阐述了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对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的反思,从而希望有助于理解现代政治的抽象性与现代人的自我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南认为,作为现代心灵的内在动力,自我意识与认同诉求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政治和政治哲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现代政治哲学把人抽象为个体,以个体为起点进行国家和民族的建构,而国家和民族也因此成为现代自我确立其身份认同的政治坐标和框架。然而,现代自我的抽象性的强大力量对国家和民族这一政治框架构成了挑战,抽象化本身的非政治倾向在自我意识的不断膨胀中呈现出来,脱离了自然与启示之规定的抽象自我在失去政治框架和宗教生活之后将进一步滑向自然状态,对现代政治认同和民主政治造成冲击,并进而威胁到现代文明自身,走向自然状态的贫乏与混乱。
以“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彰显”为主要议题的报告研讨旨在探求中国在制度上和思想上丰厚政治传统的现实境况。任军锋(复旦大学)的报告主题为“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他在政治(思想)史语境中探讨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他认为,分析本身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观照历史,可以为我们思考当下提供必要的镜鉴,探索理论,可以为我们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提供必要的洞见,公-私格局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的合适窗口。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主题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他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就是千载而下的周秦格局在近世五百年遭遇的变局。天下大势在变,周边环境在变,制度伦理在变,道心人心在变,周秦格局应变举措大约须有四要旨,一为明本,以反求诸己明中华文明之原本;一为修体,以现代国家修秦之体;一为复魂,以周孔教化复周之魂;一为立学,以文史通义立新通学。成庆(上海大学)的报告主题为“晚清士人的普世主义想象: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本文主要以康有为及《大同书》为目标,试图考察康有为在晚清转型期间如何容纳佛、道、儒乃至西方的思想资源,形成其特有的宇宙观,以及他在华夷观念瓦解之后如何型构出一种新的普世性的文明与政治认同。
对现代性的讨论无法避开宗教这一关键领域。启蒙运动的反宗教特性也印刻于现代性之中,主题为“现代性与宗教”的宗教意在探求二者的关系。刘文瑾(华东师范大学)在其报告“恶与痛:审美现代性中的主题精神”中考察了“恶”在从传统审美到现代审美中的流变。原本彰显传统价值与伦理的文学在以主体性原则和自主性、本真性为主轴的现代主义转变过程中,“恶”也由贬义变为中性甚至褒义。自文艺复兴发端,至浪漫主义确立的主体性原则,使人们迫切需要对“自我”进行探索,“再”感觉和“再”认识,而惟有借助现代意义上的写作才能让秘密不断被深入。而同时面对主体自我确认的强烈需要和现代性历史意识的危机感,波德莱尔树立了一个以孤独对抗庸众,以英雄对抗幻灭的审美辩证法的典型。然而在波德莱尔与尼采式的创举之后,对道德的僭越,对恶的体验也不免流俗,恶的平庸和悲剧的日常化成为了生活现实。张容南(华东师范大学)关注的是查尔斯.泰勒论述中的祛魅与返魅问题,揭示了查尔斯.泰勒对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韦伯所言的世界之祛魅,或曰泰勒所言的大脱嵌,描述了世俗主义的矛盾之两面: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强调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反对不必要的痛苦;另一方面,无神的现代人被夺去了以前的神灵和魔鬼,被扔进一个没人诉诸自己心灵之外的东西的世界。泰勒并不反对世俗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人本主义,但担忧一种蜕变了的人本主义,即他所说的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会将所有的意义归结为满足人的欲望和利益,它关闭了朝向超越性之门。泰勒所强调的超越,即需要通过返魅来实现。
曾誉铭(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启蒙的自我批判:生存处境、政治与宗教”中从生存境遇、共和的双重面向以及宗教-德性关联三个方面探讨了卢梭与启蒙之间的交汇与歧出,论证了卢梭不仅是启蒙思想家,更是启蒙思想的自我批判者:他的共和主义比启蒙哲人更激进,道德立场比牧师更保守,与启蒙哲人一样信赖理性的力量。曾老师认为,这种“生存论”式探寻隐藏着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思想背后都隐藏着思想者的生存,思想者们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将自己及类的生存安置在自己的思想中;同时,思想本身又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世界,它的逻辑本体超越了经验对它的质疑。而在民众利益、哲人真理与宗教信仰之间,卢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己建构的困境。
文化传统对于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塑造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主题为“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的报告研讨同时关注这两个理论与现实意义丰富的概念。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政治认同”着眼,报告主题为“保守的现代性”。他认为,在厘清中国百年来以立宪主义为核心的法治演变尤其是近三十年宪政变革的历史之基础上,展示法治变迁的激进主义困局,发掘保守主义法治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在承认激进革命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内在的弊端,从中导出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继而他指出,保守的现代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法方面,而且体现在人的生活方式、日常人伦之中。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则在文化传统的视野之中讨论了“‘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政教不同于传说中的禅让时代,如果说禅让体现的是公天下,而三代则是家天下,但三代政教在“家天下”的现实性的礼乐制度之内又蕴含“天下一家”的理想,辩证地看,此是在“家(私)天下”的历史状况中维系公天下的理想。因而,守天下以礼与取天下以德,虽然存在着内在紧张,但又被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周公政教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不考虑“家天下”,不足明周公之制礼作乐的历史局限,礼乐的讨论就会要么漂浮在“理想性”上面;不思及“天下一家”,就不足以见三代政教之理想所系,更不足以见周公制作对于中国政教的典范意义,更不足以见周公超越于时代的普遍性之所在。以家天下之势,有条件地回归天下一家之理,即为周公制作的精义。与前两位学者的讨论不同,叶斌(上海社会科学院)则以“毛泽东自由观述论”为主题进行探讨。他认为,在毛泽东早年的伦理与社会政治思想中,自由、民主都是核心概念,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不甚经意,对于宪政、法治极少论及。他的自由思想,相对于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自由思想而言,虽然在个人主义方面有所推进,但在自由政体的建构与自由权利的保障方面有所不及。
政治理论是有多重维度的,“政治理论的多重视角”的报告研讨,着眼于特定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问题。陈伟(中国人民大学)强调共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在工具的意义上将共和视为自由主义的补充,其语境是西方相对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它掩盖了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力量。在具有深厚传统主义情结及全能主义历史的国家,例如当代中国,公民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具重要性。叶浩教授在其论文《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夹缝中的两岸“和平”思考——一个价值多元论观点的理论尝试》中借由价值多元论的观点批判了两大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两岸问题中的应用。叶教授论述了价值多元论主张的“积极和平”之主张:否认和平为单纯没有战争的状态;致力于消弭历史不义,以及任何制造不义、导致不信任或提供复仇依据的条件;正视国际上已存在的各种政治、道德与法律规范,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存在。叶教授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关乎两岸的发展,也关乎人类整体的未来,将此事完全交给只重利益而忽视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件学术上与道德上皆不负责任的做法。李蕾教授在其论文“再中心化政治理论:地方性知识的流动之前景”中认为,多年来政治学的研究进展似乎反复证明了欧洲中心主义难以克服的宿命,而这一困境严重限制了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探求。通过分析中国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以及日本学者与西欧学者的中国学研究经验,她论证指出,我们不应该被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两分而局限,我们并不是完全内嵌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中的,知识的产生不是全面笼罩于文化之上,文化也不是创造知识的唯一土壤,因此,通过严肃审视知识的流动性内涵,重新中心化政治理论的各组成部分是可能的。
近年来中国社会和学界的“民国热”存在着不少失真之处,“公民与德性教育”报告研讨力图还原在一定程度上被现实想象扭曲的历史事实。沙培德(台湾中央研究院)通过分析民初的公民教科书文本,论述了其背后的教育理念——灌输学生基于个人品德的共和理想。存在于课本中品德行为训诫的,是身份认同,而且范围越大,想象的成分也就越强。民初对于“修身”逐渐重视,教育家们结合了抽象与实际的公民知识加以增补:抽象知识解释代议制度、主权、宪法和法律等诸多概念;实际知识则包含组织学生集会、以清洁运动走入社区,以及参与邻里考察。这些教科书的作用抵消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除魅(political disenchantment),又或甚至魅化(enchant)了政治领域。他认为,这些教科书反映了文化骚动,更促成了政治变迁。瞿骏(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目为“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例”。他仔细解读了1912年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在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新式学堂制度的确立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对《共和国教科书》的编撰产生了影响。《共和国教科书》的编写理念既多样又意义深远,兼备了与儒家类似的讲求伦常日用的思想和基于富强论与进化论的军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超越古今,杂糅中西。但传统的对于修身敬德的关注已经开始被细分科目的教学与对象化知识的灌输所替代,在获取智识的同时难以找到安身立命之“道”,民初教育在时人的“变”与“不变”中艰难前行。
“现代中国思潮与人物”报告研讨主要关注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思想人物——李大钊和梁漱溟。杨芳燕(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报告主题为“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从风俗保群论到第三文明论”。本文旨在探讨1914-1918年间李大钊(1889-1927)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及特质,在191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李氏个人政治立场激变过程的脉络下,思考其民族主义文化暧昧性问题的历史意涵。杨芳燕教授认为,李氏虽十分关注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面向,并且拥有一个未明言的“民族特殊性”的概念,然而从一开始,他的关怀重心即落在如何凝聚共同体的问题,而不在于如何保存民族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问题。相对应地,有关共同体的文化内容,他若非完全缄默,就是呈现详于普遍物(the universal)而略于特殊物(the particular)的奇特倾向。与杨芳燕教授从民族主义进入李大钊思想不同,段炼(台湾中央研究院)从超越性视角来理解李大钊的思想,其报告题目为“寻求超越:以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为中心的研究”。他认为,在李大钊的思想世界里,与他反思并体验超越精神、试图重建价值体系密切关联的,是三个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取向。它们分别是“心”的取向、“我”的取向与“今”的取向。作者试图通过对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思想的分析,试图探究这一时期中国式的超越精神及价值诉求所呈现的特点,并进一步阐释世俗时代的超越精神与传统思想之间既断裂又连续的关系。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主题为“梁漱溟的国民性话语批判”。他认为,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里,存在两套相关的话语系统,一套是民族国家和国民性话语,另一套是文化自觉和人心话语。他对两者都有所论述,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投身于乡村建设之后,他更倾向于第二种话语,而对民族国家和国民性话语逐渐采取批判的态度。本文试图梁漱溟的这两套话语系统做一个简要的剖析。
最后,与会者参加了以“现代政治与认同”为中心议题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就“不同视野中的国家认同”与“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籍由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和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主题发言,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将相关问题的讨论向更深层次推进
通过此次研讨会,与会者对“现代认同”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交流,在现代认同的多元性、中西视域的交汇等问题上达成了颇具意义的共识,为今后更进一步的学术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手机版 | 归档 | 关于我们| (粤ICP备14048290号 )
主办: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B座7楼学术研究杂志社
邮编:510635
© 学术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